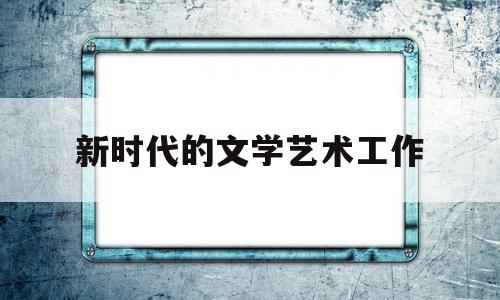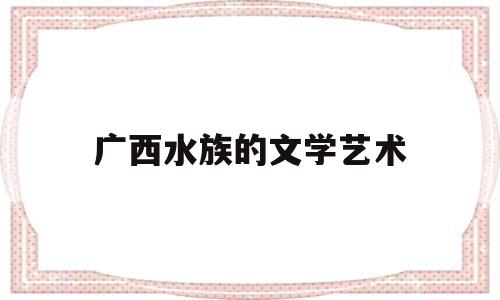莫言和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作为中国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其文学创作与百年中国文学的写作是紧密相连的。通过对莫言小说的阅读,可以发现在他的小说中鲜明体现出了一种“田野”意识。这种“田野”意识不仅表现在“说书人”立场的确立上,也体现在“田野”的独特空间特征上;莫言小说的另一特征在于向读者展示人性当中的“朦胧”地带。这两方面的努力成为了莫言在世界文坛上获得相应地位的原因。
诺贝尔文学奖开始的时间是1901年,而此时中国文学也在发生着变化。回顾这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与中国的政治历史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一直交织着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的纷扰对话。百年汉语写作中,“诺奖情结”可谓是大多数作家和评论家心中“永远的痛”。
在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西方文学的影响一直都存在,从陈独秀坚持的“以欧化为是”、胡适提倡的“输入学理”,到20世 纪80年代的新潮小说的兴起。我们一边向西方学习以求完成艰难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我们又有很清醒的意识:这是属于西方的东西,我们终究要有属于自己的文学价值观。李敬泽曾提到:“被两种不同的自我想象所支配:一种是被侵犯、被剥夺的软弱和愤怒,另一种则是接受侵犯者和剥夺者的逻辑,终有一日会消除我们的软弱。两种想象 其实是相互派生的,在它们各自内部都涌动着‘力’的焦虑。”
《红高粱家族》
这种焦虑不但体现在当代小说家的叙事技巧层面,更核心的问题可能还在于如何合理的表达中国经验,合情的展示中国想象力,并且可以获得包括西方世界读者在内的认同。英国莫言研究者杜迈克在评论中提到的:“像很多同时代的‘后毛一代’的作家一样,莫言试图着把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的文学技巧相结合,将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思想进行想象性的转化,由此创造一种表达他个人声音和视野的纯粹现代中国式的叙述风格”。
这种追求体现在他的小说叙述中就是一种鲜明的“田野”意识。同众多获奖作家一样,莫言在他的作品中探讨了诺奖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就是对人和人性的复杂性给予了相应的关注,更准确的是对人性中的善恶难分的一片模糊地带给予了集中的展示。故事的外形终归是个“幌子”,人性中的美好和坚韧才是表达的重心。
莫言的“田野”意识
纵观莫言在中国文坛上的表现,我们会发现,他在批评家眼中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但没有小说家可以为莫言的小说轻易贴上标签,更无法用任何一个流派特征来涵盖他的作品。我们在他的评论性文章中能发现这些关键词“泥沙俱下”、“语言的巫师”、“汪洋恣肆”、“天马行空”等等。在这些抽象词语背后,我们隐约感受到了莫言小说与当代众多小说家有着不同之处。
我们发现,当其他的小说家都急于在小说中讲述自己的故事,发出自己的声音,急于追逐西方小说中的叙事技巧,急于从纷繁的现实社会中寻找所谓深邃的意义和思想时,莫言却坚持了一种独特的方式讲述着山东高密东北乡。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就是“说书人”的方式。
有评论家认为在莫言的小说中有复调叙事的特征,这种复调展示为互不相属的个体在面对同一世界时,由于不同价值标准和观念而发声,最终达到对这个世界更为全面的解释的目的。这些看似纷繁杂乱的“声音”所言说的世界其实才是真实的世界。
其次,小说家与读者的关系在当代其实并不是很融洽的,小说家只负责写出自己的作品,读者的喜好暂放一边。但我们在观察莫言的小说时,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不用过于担心他在小说中向读者隐藏了或者阐释了些什么,他不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启蒙者,也不像一个表情严肃的说教者。这一叙述角色的确立,使得莫言的小说与中国传统古典小说建立了一种精神上的联系。这其实是一种优秀的小说伦理,他的伦理取位在民间,人们自古以来就喜欢听那些在“田野”中发出的稀奇古怪的“声音”。同样也只有“田野”是诞生这些“声音”的宽广舞台。而“说书人”是“田野”上的精灵。
我们去关注莫言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从“我爷爷”、“我奶奶”、沉默的“黑孩”,到蓝脸、罗小通、蝌蚪等,这些人的身上都带有“田野”上的特殊的野性和传奇色彩。他们一出场,气场明显与其他小说家笔下的人物不同。
莫言的“田野”是记忆中的“田野”。莫言曾经谈到,故乡其实是童年记忆中的故乡,在这个故乡中,莫言和他的笔下《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最为相似,他在生活中沉默寡言,但是身体的其他感官无比敏锐,与“田野”中的一切植物和动物都是通灵的。这种通灵感受衍生到他的其他小说中,便体现为一种神奇瑰丽的、魔幻的色彩。这种魔幻的色彩像极了他的同乡蒲松龄。
《我与加西亚·马尔克斯》
莫言等 著
当莫言看到拉丁美洲的马尔克斯写出极富魔幻色彩的《百年孤独》时,他的感慨是:小说也可以这样写的。这些魔幻色彩的故事在中国高密的“田野”上正是他儿童时期的记忆,“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
由此我们可以探索出莫言作为一个执迷的“说书人”,他讲故事的立场在“田野”,他的故事的来源也在“田野”。“田野”这样一种无限延伸的空间和区域,它是辽阔的充满生机的。是想象力展开的天然舞台,是一片可以混淆善恶伦理的世外桃源。在这片“野地”上,乡村生活中诸多无法逃避的生存和命运的沉重都可以在此变化为一种轻盈。
正如我们不会去追问黑孩到底有没有看到《透明的红萝卜》?姑妈的宝刀到底有多么的锋利?我奶奶是不是那样的—个风云人物?这样我们再次阅读莫言的小说时,就可以体会到他在讲出他的故事时内心是多么的自由和快活。在小说外他是一个懦弱的人,但在小说里他是一个“胆大包天”的“狂徒”。他的“田野”,就是他记忆中的山东高密东北乡。这一点与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与福克纳的约克那帕塔法又是何其的相似。从这个角度上说,莫言与马尔克斯与福克纳之间建立的是一种更为内在的精神上的联系,而不在技巧和方法。
莫言对“朦胧地带"的书写
莫言笔下塑造的一系列典型的人物形象:如黑孩、暖、“我奶奶”、蓝脸、姑姑等。我们在分析这些人物印象时会发现在他们的身上具有着一种非常相似的特征,那就是对人性当中朦胧地带的展示。
在《透明的红萝卜》中,我们总会对那个命运坎坷但具有坚韧忍耐力的黑孩产生兴趣。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村中成长的孩子,带有农村社会中特有的淳朴、诚实、自卑和极强的自尊心,当然还有他身上的传奇色彩。黑孩对菊子的情感可以说是当代小说中塑造的诸多情感中最为让人动容的一种。我们到现在为止也很难说清楚这种独特的感情是一种什么样的具体感受,菊子在黑孩心中是女神,但女神当众怜悯他,他却在她的手腕上狠咬一口。当他发现菊子和小石匠在一起时,仇恨促使他在小铁匠和小石匠打架时,帮助小铁匠来打翻他平常的保护者小石匠。这种独特的感情正是人性中的一片模糊地带,其间没有善恶,日常伦理难以规范。
《丰乳肥臀》
在当代文学史上,类似情感的书写都获得了读者和评论家的极大的认同。茹志鹃的《百合花》中,“我”、新媳妇在面对小通讯员的死的时候的内心感受、张汉的特殊感情,它们都是作者对人性中最为神秘和纯净的一种情感的传达,这种情感超脱了日常生活、时代,甚至超脱了社会伦理道德,但它却合乎最为高贵的人性。如果说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窥视人性的角度选取的还是—个孩子的内心,在《白狗秋千架》对主人公暖的书写就更为外现。“我”和暖的命运在—场秋千的意外中发生了变化,“我”参军离开故乡,暖嫁给哑巴,一胎生了三个哑巴儿子。“我”再次回到故乡时见到了暖,原本—个鲁迅返乡式的故事在莫言的笔下竟演变成另一番场面
“分开茂密的高粱钻进去,看到她坐在那儿,小包袱放在身边。她压倒了一边高粱,辟出了一块高间,四周的高粱壁立着,如同屏风。看我进来,她从包袱里抽出黄布,展开在压倒的高梁上。一大片斑驳的暗影在她脸上晃动着。“好你??你也该明白??怕你厌恶,我装上了假眼。我正在期上??我要个会说话的孩子??你答应了就是救了我了,你不答应就是害死我了。有一千条理由,有一万个借口,你都不要对我说。”
暖作出的选择既不是源于正常的通奸偷情,也不是报复举动,这样的选择正是这个残疾的妇女在面对生活中的不幸命运时的激烈反抗。这种反抗的根源也许就在于:人性中对一切美好的梦想追求的过程中落败的一次绝望的反击。暖的举动无疑是人性中爱恨交织的一种表达。从这个角度来看,暖的选择堪比《呼啸山庄》中的希克利那绝望的爱。以上两篇都是莫言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在新作《蛙》中对姑姑形象的塑造也让人慨叹。
《蛙》
早年的姑姑是送子观音,被人称为活菩萨,计划生育实施以后,姑姑变成了夺命的刽子手。我们仔细辨析,莫言的本意并不在对计划生育本身的赞扬或反对,这一基本国策原本就是与中国文化、传统、政治、伦理、金钱等纠缠在一起的复杂活动。当姑姑置身于这一混流中,并有着坚定的政治选择时,悲剧就已经诞生。我们可以继续追问下去,姑姑为什么有这样的政治选择,为什么要坚守计划生育的政策,这样写下去无疑就是一部批判现实的力作。
但莫言并没有选择这样来写,他重点关注了姑姑早年与后来的两种不同选择,并且叙述了姑姑在老了以后,心中的忏悔与赎罪,这些都涉及到了人在面对弱小的生命时的一种复杂态度,你可以给他生活的机会,也可以轻易的让他死亡,这种主宰的权利成为考验人性的一个试金石。姑姑给人接生,带来新的生命;姑姑又让人引产,终止新的生命;姑姑看到要生产的牛时,人性书写达到一个顶峰:见母牛下跪。眼泪哗哗的下来了,这些又都写出了姑姑的内心的柔软与善良。纵观对“姑姑”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的复杂,实为对意识形态和人性观念在面对生命时是敬畏还是漠视给予了复调式的讨论。
莫言在获奖后发表的获奖演说《讲故事的人》中提到:“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与他的其他作品类似,莫言对在历史、特定时代、特定事件的书写都是一种寓言化的书写,重点在于对这些历史境遇下的当代乡村中农民的具体境遇中的或幽暗或明媚的人性进行展示,这样的书写是高密东北乡的,是山东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回顾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时代与文学始终纠缠不清,更多的时候,文学陷进了时代的漩涡,被时代裹挟。
文学或成为“传声筒”、或成为“匕首,投枪”、或成为思想、真理的“载体”、或成为“欲望化”的符号。一种健康的、真实的,被命运和自然所折磨的复杂人性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过了。对这种善恶难定的人性书写不是简单、附和式的认同,而是经受生活和命运考验出来的真理。在这个维度上,莫言和他的小说展示了文学存在的价值和维度。
今日话题
你读过莫言的什么作品?你是如何评价的莫言的作品的?
END
| 发送“书单” ,你喜欢的各类书都在这里 |
| 发送“一句” ,来和小编一起抄句子吧 |
| 发送“共读” ,千万书友等你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