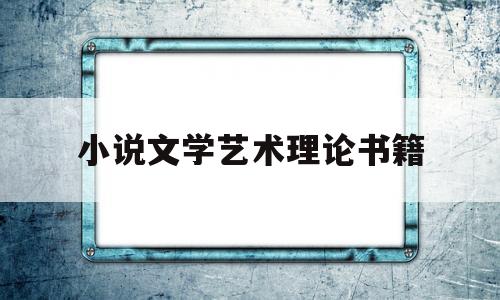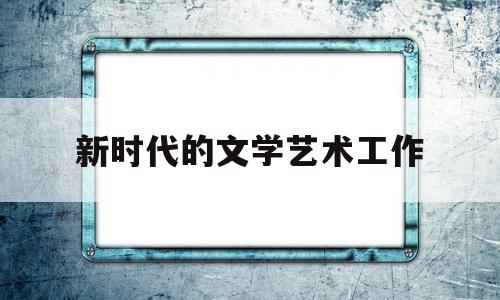清人焚稿现象的历史还原
罗 时 进
康熙十年(1671)二月初五[1],在清代历史上本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但周亮工将大量著作“尽付咸阳一炬”的惊世之举使这一天载入了清代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由于周氏在明末清初具有的地位,以及此事的特殊背景,其焚书事件一时间影响巨大,许多文人对此发表评论,其中吕留良所言带有对焚稿作为一种“文化行为”的总结意义:“古之人自焚其书者多矣。有学高屡变,自薄其少作者;有临殁始悔不及为,谓此不足以成名而去之者;有刺促恐遗祸而灭者;有惑于二氏之说,以文字为障业者;有论古过苛不敢自留败阙者;甚则有侮叛圣贤,狂悖无忌,自知不容于名教,故奇其迹以骇俗而自文陋者。其焚同,而所以焚不同也。”[2]这里对焚稿原因的分析虽然基于迄至周氏焚书前的现象,但对清人焚稿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借鉴作用。不过清人焚稿行为之烈、规模之大、所涉之广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代,一部分焚稿原因也超出了吕留良当时观察的范围。大致说来,可归于“社会意念”与“文学行动”两个方面。当然这两方面难以判然区分,也难以完全涵括,如“悔其少作”现象,颇多沿承自古以来的文人传统,往往是以对“青春文字”的否定显示“老成境界”,既非出于某种社会背景,也难说出于文学自觉。焚稿的因素相当复杂,本文仅择其要、示其概,试图通过初步的现象分析,还原历史现场,寻绎某些特殊历史事件的脉络。
一 “焚诗谢是非”:走出“紧张”的社会关系
人非自然存在物,具有社会属性。由于社会分化,每个人都处于不同位序的社会阶层,而各阶层之间因固有利益和文化价值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紧张关系。对清代这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言,文人极致化的紧张关系体现在与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集团之间。一般而言,离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集团越远,心理越松弛;反之,离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集团越近,或介入其中,则紧张度越高。问题恰恰在于,或因原有的家族地位,或因科举带来的社会流动等诸多原因,清代大多数文人都参与了广义的统治阶层的活动,因而紧张感是一种普遍的存在。
明清易代之际,是努尔哈赤集团争取统治权和巩固统治秩序的时期,其时整个社会处于纷孥惶骇之中,随之而来的江南“三大案”形成的巨大压迫感传导为各阶层文人内心的高度紧张,人们必然采用某种方式加以释放。焚稿,无论出于内在抗拒心理,还是被胁从,无疑成为减轻压迫感和走出紧张社会关系的选择,因此明清易鼎之际直至康熙初年,成为清代文人焚稿的高峰期。
此际焚稿这种特定的个人隐私行为成为跨代文人的群体意念,然而各自的心理并不相同。吕留良当“甲申北都陷,庄烈崩,光轮号泣呼天,尽焚其平日所为文,散家财结客,思复大仇。往来湖山间,栉风沐雨,艰苦备尝”[3]。陈涣在国变后内心愤然见于辞色,“尽焚其诗、古文,避深林中”[4]。刘若宜于京师陷后投缳自尽,为家人所救,“遂僧服遁居甑山,三十余年未尝入城市,所作诗文尽焚其稿”[5]。施显谟乃前明内阁中书,入清后不仕,“临殁时尽焚其所作”[6]。以上,吕留良的焚稿行为是复仇心志的激烈表达,陈涣、刘若宜是隐居前的精神告别,施显谟则是政治幻灭后身与心同归圆寂。此际更多的焚稿是为了避祸,正所谓“焚诗谢是非”[7]。吴伟业记彭宾语曰“吾之诗以散佚不及存,以避忌不敢存”[8],傅山录《鬼谷子要语》曰“寡言则途坦,焚砚则心安”[9],都反映出一代人的真实心态。另外,顺治年间有一批文人出于各种原因北上入阁,亦往往将过去所作文字付诸回禄,如王铎“清顺治三年(1646)赴京前,焚其诗文稿千余卷”[10]。在转变身份前所做的这种自我清理,显然是为了与统治体制相容无碍。
从顺治朝到乾隆朝,清廷一直存在着巩固统治地位的焦虑与警觉,其背后隐藏着对文人阶层相当程度的警戒心理。各种笼络手段的采用,只是试图扩大其精神一统的版图,但深层的防范意识未尝松懈过,对文字之防尤为重视,禁毁之厉堪称空前。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案发,都御史赵申乔参奏:
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膺恩遇,叨列魏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其容滥厕清华?[11]
既为臣属,“今膺恩遇,叨列魏科”,就必须“追悔前非,焚削书板”,否则便属于大逆不道。正因为如此,乾隆年间因修《四库全书》而展开大规模焚销行动,“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12]。这使得士林群体骤然震骇,深感“今日儒运,恐遭焚坑,清流之祸不远矣”[13]。金堡因所作“语多悖逆”,遍行堂板片“委员解赴军机处,查销在案”,且令“诗集之外,尚有碑记、墨迹等类留存寺中,亟应毁除净尽”[14]。徐崧等人合辑《诗风》,而所刻“选本《怀音集》《缟纻集》《南字倡和》《九日倡和》诸集,不啻数千页,俱以讹传禁诗,悉付祖龙”[15]。清人学术著作与文学创作之多,是历代无法比拟的;而清人焚文毁板数量之巨,烟燎灰飞,同样是古往今来无与伦比,对此后人痛惜浩叹不绝于耳。
清代文人的紧张心理,并不止于与努尔哈赤最高集团之间,也体现于官僚体制内各阶层之间。官僚集团内部的冲突施加于个人,受压力者在危机感、失败感和绝望感下往往产生焚稿这种自虐性意念。周亮工康熙年间因卷入“漕运案”,闭门待罪十个月,又逢丧弟的打击,如在汤镬,心绪如乱丝,百苦相煎,觉得人生已毫无生趣。不幸的是“庚戌再被论”,故而“忽夜起仿徨,取火尽烧其生平所纂述百余卷,曰:‘使吾终身颠踣而不偶者,此物也。’”[16]吕留良《赖古堂集序》对这一事件的解析最为精辟:
(亮工)豪士壮年,抱奇抗俗,其气方极盛,视天下事无不可为。千里始骤,不受勒于跬步;隐忍迁就,思有所建立。比之腐儒钝汉,以布衿终敛村牗,固夷然不屑也。及日暮途歧,出狂涛险穴之余,精销实落,回顾壮心,汔无一展,有不如腐钝村牗之俯仰自得者。吐之难为声,茹之难为情,极情与声,放之乎无生。彼方思早焚其身之为快,而况于诗文乎哉?[17]
文字乃人生之记录与表现,当人生已至于绝境,愿以焚身为快,文字又何足爱惜?如此,烬燃诗文便是一曲“人琴俱亡”的生命绝唱了。这里不妨再看梁鼎芬焚稿事件。梁鼎芬,字星海,号节庵,番禺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任知府、按察使、布政使,性为骨鲠之臣,屡劾权贵,未尝畏惧。在中法战争中,权力核心层的李鸿章一味主和,梁氏因弹劾其六大可杀之罪而触怒慈禧。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云:
节庵早岁登第,以论劾合肥罢官,年甫二十七,士论称其伉直。晚以南皮疏荐复起,壬癸以后,征侍讲幄,琼楼重到,金粟回瞻。悱恻芬芳,溢于篇什,尝自言“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出”,遂焚其诗。[18]
其焚稿时有言:“一切皆不刻。今年烧了许多,有烧不尽者,见了再烧,勿留一字在世上。”[19]梁氏焚诗与历史大变局或无直接关系,主要是与官僚阶层内部形成重大矛盾。当他深感“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出”时,焚稿则迫不得已了。清人每有进谏陈奏“疏上辄焚稿,故人无知者”[20]的情况,也多见友朋被祸后“全焚诗笔留心血”[21]之举,都深含着对官僚关系网络的高度警惕。
“花因刺眼偏多种,诗为伤心欲尽焚”[22],是清代士林阶层相当普遍的现象。李驎《许君平先生小传》记载:“许君平先生者,兴化诸生许坦也。少负意气,务上人,视天下事无一可当意者,然竟不偶于时,所遇辄穷,屡试屡蹶,遂尽焚弃其所为文,放浪歌曲以抒其愤懑不平。”[23]显然,无论人们怎样用“避人焚旧草,非有不平鸣”[24]向社会表白,总无法遮掩焚稿乃缘于伤心的事实。男性文人所经历的社会冲突与人际紧张各有不同,而对女性来说,则有一种殊途同归的人生宿命。
应该承认,较之以往历代,清代女性的文学境遇无疑是最好的,女性文学社团活动时有可见,“雨后怜香花共摘,风前射覆酒同斟”[25]的情景表明其精神空间有所扩展,甚至有女诗人“急于求名,唯恐人不及知。而未定之稿,出以示人,求片言于大佬名公以为荣”[26]。故所存作品数量也很可观,胡文楷先生《历代妇女著作考》自序说“清代妇人之集,超轶前代,数逾三千”[27],这虽然是一个很不完全的统计,也已远远超出清代以前女性作家作品存量的总和了。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清代女性创作较为有限的一部分,其所焚、所弃作品之夥是惊人的。她们的作品为什么难以流传和存世?袁枚、王文治的诗弟子骆绮兰在《听秋馆闺中同人集序》中道出的部分缘由多为人们引证,然而她所谈及的闺秀“幸而配风雅之士”,自必爱惜其作品,故“不至泯灭”;而“所遇非人”则必“将以诗稿覆酰瓮”[28]等,涉及的只是家庭内部问题,虽不无根据,但未触及女性进行文学活动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多少有些流于皮相。其实对清代女性文学创作造成困扰和限制的最大力量,仍然是传统礼教范畴的“妇德”。杭州夏伊兰作《偶成》云:“不见三百篇,妇作传匪鲜。《葛覃》念父母,旋归忘路远。《柏舟》矢靡他,之死心不转。自来篇什中,何非节孝选。妇言与妇功,德亦藉此阐。”[29]在女性自身的视野中,自古文学经典关涉女性者皆教化之选,妇言、妇功、妇德作为道德约束,直至清代仍然是女性无法根本走出的精神樊篱,所以作品随写随毁或临终付诸一炬,成为本然的自觉意念[30]。
较早的女性焚稿事迹见于唐代,《北梦琐言》卷六载进士孟昌期妻孙氏善为诗,而一旦焚之,“以为才思非妇人之事”[31]。至明代,其特定的崇尚程朱理学的人文生态使得女性焚诗成为寻常之事[32],而有关清代女性碍于礼教闺范而焚稿的记载几乎随处可见。丁丙《国朝杭郡诗三辑》记载杭州才女包韫珍:
年十四即能诗,其父戒之曰:“女子无才便是德,古之福慧兼修者几人哉?”乃深知韬晦,然结习未能忘也。后承外叔父朱秋垞先生教,诗益工。……比适庄氏,愈郁郁不得志,仍依母食贫,其《自序净绿轩诗稿》云:“焚弃笔砚,顶礼空王,发生生世世永不识字之愿。”其生趣可想矣。[33]
何绍基《汤母杨太淑人吟钗图记》云:
汤公楚珍之配杨太淑人,幼学工诗,有才女之名。年三十五,楚珍公杀贼殉父于凤山县,太淑人以抚孤不得死,尽焚其前所为诗,后不复作,得节妇之义。[34]
女性焚稿在自卑与伤感之外,也表现出某种伦理洁癖,隐含着对文学史家向来将其边缘化,甚至将其作品与方外、青楼女子合编做法的抗拒。顾贞立《焚旧稿》诗云:“临风挹泪奠霞觞,几载闲愁一炬偿。何事忍教成蝶去,肯容流落俗人囊。”[35]这几乎可以看作一篇清代女性焚稿的“宣言”了。
正是出于对壸范的坚守与对流俗的拒绝,众多女性诗人在易箦时往往将所有作品尽付祝融。这类事迹触目可见,如沈德潜《清诗别裁集》记载长洲女子韩韫玉“工词翰,年三十时,著述已富,病殁前,尽取焚之,不欲以文采见也”[36]。郭善邻《张母刘夫人行实》:“夫人故工诗。……病革忽执册语侍人曰:‘妇人之分专司中馈,此余闺房哀怨之句,留之将何为乎?’命投烈焰中。”[37]徐起泰《继室倪孺人行略》记叙倪氏“(乾隆)辛亥七月,忽遘疾,廿一日疾剧。予出延医。孺人自知不起,与公姑泣诀,随命婢尽焚所作时艺约二百余首,古文约百五六十首,诗约千余首。予归咎之,呜咽叹曰:‘妾一生谨慎,计犯天地所忌者此耳,曷用留之以重予罪!’言讫而逝”[38]。让平生文思浴火成灰,抹去一切与闺范不符的色彩,不留任何人世口实,是摆脱与社会紧张关系的最彻底的方法,也成为清代女性文人最习见的人生告别仪式。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无论男性作者还是女性作者,都无法彻底摆脱社会尘网。文学作品一方面用作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具有纾解心怀的功能;一方面也造就压力,成为非自在之物。因此在特定条件下,必将产生焚稿这种非常态的意念。清代男性入仕文人之焚稿,除顺治时的“贰臣”外,多在被祸、罢官或临殁时[39];女性文人则往往在出嫁、寡居、皈佛或病革时,都具有人生情境发生重大转变的特点。他们有关爨稿的解说,皆可看作对人生抱持哀绝心理的悲壮证词,其笔锋所向并非文学世界,而是沉重的社会和历史的大幕。
二 “诗多焚稿兴逾深”:重新审视文学创作
大约从中唐开始,文人便逐渐形成了“日课一诗”的习惯。宋人推广此法,将诗歌创作视作“士”的精神追求,后人更将其视作“士”的日常生活方式[40],并将其扩展到其它文学门类。时至清代,文字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文学的崇高感和文人的优越感已较为淡化。极为日常化的文字业难免产生一定程度的写作疲惫,从而引发对文学价值的思考。清代大量焚稿现象的存在有其复杂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与人们重新思考文学概念,审视文学价值具有内在联系。
在这个问题上,八股文这片长期笼罩清人的阴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对于许多清代文人来说,摩挲文字的初始方向在于举业,最易被否定的也是八股文字,而无论热衷于此还是厌弃此道,都往往以焚稿作为行动的标志。
先看热衷者。到清代八股文已经流行了二百多年,其弊人多知之,但其利更诱惑人去追求。八股文与传统文学所形成的价值分裂是显而易见的[41],清人深知:“文无所谓今古也,盖自制义兴而风会趋之。学者习乎此则纡乎彼,于是遂视如两途。”[42]与古文相比,韵语与制义之间的畛域更加分明,所以毛奇龄劝诫:“习举义者,戒勿为诗,而为诗者,谓为举义家,必不工。”[43]为了防止“旁及者必两失”[44],也只有辛苦数年先拼个通籍再说。清初曹贞吉即如此,长期困顿科场后“益自奋厉,博极群书,篝灯雒诵,深夜不休”[45]。为专志于科举,不仅不赋诗章,更焚烧了旧稿。其《岁暮感旧抒怀二十八韵》云:“丙申游帝都,归来遂决计。读书唯小园,矢怀一何锐。不谓两放逐,失我凌云势。痛哭焚旧编,誓欲绝匏系。淹屈负须眉,举止惭仆隶。”[46]在挣脱匏系牵绊的努力中,首先用烈炬摧毁了通向文学大殿的路标。
再看厌弃者。科举中的失败者总是多数,当通籍无望时,举业程文便如敝屣,当归回禄之神了。温斐忱《董若雨先生传》载录董说焚烧科目文章之事:“时流寇方躏中原,而中朝各争门户,先生独怀隐忧。未几罹闯祸,慨然曰:‘吾家累叶受国恩,今遘数阳九,纵不能死,忍腆颜声利之场乎?’遂弃诸生,焚其十年来应举之文,著《甲申野语》。”[47]康熙时张坚博学多才,“原是江南一秀才”,文章词赋脍炙人口,但“少攻时艺,乡举屡荐不售。焚稿出游,转徙齐鲁燕豫间。……交游日益广,而穷困如故也”[48]。作为专为举业而模铸的敲门砖,制艺重复性写作的数量极多,内容偏枯,性情寡淡,即使那些成功者也深以为耻,嘉庆间进士谢兰生“博通多能,精时艺,暮年悉焚其稿,曰‘此仅足弋利禄,不可传’”[49]。
文人立言,在当世是立足文坛或进入公共领域的资本,对未来则可能成为扬名立万的凭依。八股名家虽不乏文学成就非凡者,但那终究是禄利之筌蹄,其功利性取向和应用化功能决定了这一文体不可能在具有审美属性的文学殿堂中长期占据显要位置,大量的八股文最终被掷付祖龙,确乎符合艺术逻辑和历史逻辑。但客观而言,清人焚稿,时文只是一个部分,而真正成为文化事件的焚稿还在诗文和学术著作方面。
康熙时汪淇曾说:“五十年之前,见一作诗者,以为奇事;三十年之前,见一作诗者,以为常事;沿至今日,见一不作诗者,以为奇事矣。”[50]由此清代诗人之多、作品之繁可以想见。近三百年中,诗歌这一文学河汉中最为明亮的星斗,文化老树上永远不落的神果,时时被揣摩、欣赏、应用着,虽然在真正的诗人那里崖岸自高,仍是带有精神特性的艺术构造,但在泛文人群体中,则几乎变为一种文字构件,可以批量化生产了。诗歌如此,其他文体同样存在创作专业性降低和内在精神消解的现象,文学知识的普及化和创作行为的大众化是有清一代的总体倾向。在这一环境中,精致与粗糙、高雅与通俗、专精与庸常并陈杂现。面对数量极大的作品,不少文人深感“夸多斗靡,非性所好”[51],因此除庸去冗成为清代文学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诗多焚稿兴逾深”[52]的现象引人瞩目。
清人焚诗承继了前人“悔少作”的审视方式。宋人在倡导“日课一诗”时,对日常写作稠叠洊至,作品水平参差不齐,也颇知其弊,形成了内省俟善的自觉。宋祁《笔记》云:“‘余于为文似蘧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几至于道乎?’每见旧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烧弃。梅尧臣喜曰:‘公之文进矣。’”[53]对过去创作的审视,往往聚焦在初始阶段,从“悔少作”变为“焚少作”。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序》云:“始七龄,蒙先子专授五七言声律,日以章句自课,迄元佑戊辰,中间盖半甲子,凡著之稿者,何啻五六千篇。前此率三数年一阅故稿,为妄作也,即投诸炀灶,灰灭后已者屡矣。”[54]陈师道、杨万里、徐府等一批作家都有焚毁“少作”之举[55]。清人对“少壮诗篇总未工”有更为深切的体会,“焚却从前快意诗”[56]的现象屡见不鲜,这里聊举几例。
李伍汉《郑慎子诗叙》云:
忆十年前,从宪武斋中得《余全人诗刻》读之,喜其风流掩映,郁勃生姿。问其年,少余二岁,余因取少时诗草尽焚之。[57]
章藻功为汪无己《焚余诗》作序云:
无己学问纳新,文章吐故。理卞和之璞,何曾稍掩其瑕;禀西子之容,窃恐偶蒙不洁。鬓已齐而犹略,尚叹飞蓬;腰欲细而为纤,渐同辟谷。因自削其少作,俾共信夫老成。[58]
方东树《半字集序录》云:
余年十一,尝效范云作《慎火树诗》,为乡先辈所赏,由是人咸以能诗目余,余亦时时喜为之。丙子遭忧,灰心文字,兼悔少作,遂尽取而焚焉。[59]
虽然文学史上不乏天才出少年的佳话,但初辨音声时,难免以齞唇历齿之形,作巧笑微颦之态,故而“庾信文章老更成”大体可以看作一般规律。李伍汉、汪无己、方东树在稍近老成时,从比较审视中发现年少时依口学舌实在稚嫩难掩,骈俪绮靡之思也不宜示人,故严格拣择,以今日视昨日之非的姿态,将“少作”尽付烈炬,挥手告别青春写作。
清人与青春写作决绝的告别态度,既是传统习惯的复制,也是成长心理的反映,但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的是对文学价值和文学理念的守护。长期浸润在文学生活中,难免对作品的质量产生某种钝感。钝感是一种审美疲惫,文学品质、价值的敏感性为写作娱乐或日课程式所消磨,既无意于自我谛审,也无法清晰辨认作品质量高下。然而经过长期学养积累,在特殊的境遇抑或他者视角的照察下,会重新唤醒文学审美意识,通过自觉的检视,发现过去作品的庸劣。对照清人的稿本与刊本,可以看出一些作家修改完善的痕迹,但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自羞于“诗剩累千篇,幸少惊人句”[60],而进行选择性、筛汰性的焚稿,过激者则倾囊而出,付诸一炬。这种行为,清人戏称为“火攻”。张煌言对“火攻”曾作分析,其《陈文生未焚草序》云:
祖龙一炬,六籍烟飞,然博士掌故,犹未焚也。迨咸阳三月火,而经史无余烬矣,乃后世不罪羽而罪政,何哉?殊不知枢不蠹流不腐。文章一道,倘陈陈相因,毋宁付之祝融氏之为快也。究之秦皇焚书而书存,汉儒穷经而经亡。呜呼!是岂焚之罪也哉?况乎风雅之林,日趋于新;而动辄刻画开宝,步趋庆历,譬之寒灰,其能复然乎?夫焦尾之桐,出爨而宫徵始发;火浣之布,经焰而色泽弥新。物固有待焚而成其贵者矣,胡陈子文生则又以《未焚》名篇乎?嘻!吾知之矣。年来烽举燧燔,奚啻秦楚之际,几疑此日乾坤,劫火洞烧,而文生夷犹其间。每遇名胜,辄欲焚鱼;凡经倡和,都令焚砚。一吟一咏,簇簇生新。若钻燧槐榆,递相迁代,非未焚也,盖有不可焚者在焉。余因谓文生:法言有之,火灭修容,戒之哉!火攻固出下策矣。[61]
张煌言认为,劫火洞烧时焚鱼(弃官)与焚砚都是不得已之举,一味“火攻”,乃属“下策”,可以赞赏的是:“文章一道,倘陈陈相因,毋宁付之祝融氏之为快也!”
毋庸讳言,清人写作最突出的问题是易开平庸之花,有骨架无骨力,有文采无精神,有记叙无理致,有技巧无境界,这些皆属平庸。而在前代文学典范面前沿袭模拟,生硬地唐临晋帖,“学汉魏则拾汉魏之唾余,学唐宋则啜唐宋之残膏”[62],乃最不可不戒之平庸。康熙时李嶟瑞曾模拟诸家,“某篇求似某篇,某句求似某句,亦殊沾沾自喜,而不知其为已陈之刍狗”,后乃自羞于“易吾之面为古人之笑貌……翻阅笥中,取所为诗,悉焚弃之”[63]。叶燮弟子薛雪更以笔意出新为追求,凡“作诗稿成,读之,觉似古人,即焚去”[64]。相比较而言,道光朝林仰东(子莱)的学古态度较为平允,林昌彝《林子莱诗集小传》云:
子莱幼颖异绝人,年十一,辑唐人诗为古近体,传观遍冶南。余识子莱于刘炯甫席间,随与之定交。子莱甫冠,负不世才,所至魁其侪偶。诗初学随园及十砚翁,余力劝其取法乎上,子莱遂焚其稿,肆力于汉、魏、三唐、宋、元、明诸大家。年三十,诗境日益进,上自汉、魏,下至唐人高、岑、王、李诸家,莫不登其堂而哜其胾。[65]
明人在文学观念上表现出强烈的复古意识和宗派倾向,并以之左右创作路径,甚至以焚毁某种作品作为文学观念的宣示和流派皈依的标志。清人为文自有与明人相同的不苟态度,但文学观念的排他化、不同取向的敌意感[66]、汉魏唐宋的偏好性都较淡薄[67],表达得较多的是对“正法”“工致”的祈求,具有显著的内省性特征。如乾嘉诗人钱申甫得王次回《疑雨集》,“大赏之,旦夕吟讽,多拟为闺房赠答、怀人咏物、缠绵旑旎之作”。陆继辂见其未循正法,乃“力规之”,钱氏“遂尽焚其稿,而放笔为歌行,横空盘硬,抑塞磊落”[68]。王培荀《听雨楼随笔》记录乾隆举人周立恭“好云性,好为诗,而成篇即焚弃,自嫌不工”[69]。单学傅《海虞诗话》称道光朝姚柳堂“诗承家学,刊有《支川竹枝》百首,并七律二卷,余尚千首,中年疾亟,自谓未工,命家人悉焚之”[70]。冯志沂《送余小颇先生出守雅州序》云:“志沂幼失学,自应试文外无所措意,通籍后始为诗,又好随俗为纤靡之音。戊戌春,于友人所见小颇先生文,求介以见,因呈所为诗,先生涂乙过半。心初不能平,徐取古人诗读之,乃始恧然愧汗,悉取旧作焚弃之。”[71]这类事迹载籍遍书,不胜枚举。
显然,此种焚稿主要出于文学范围内的一体之念,乃通过对文学生产的直观和体验,照察境界不高的作品,针对自我和他者眼中的失败之作,进行矫正与净化。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可以将清人对庸烂之作的摧纸扬灰行为看作一种学风分叉。在其内省自觉和向善启真的思想倾向中闪烁着一代文人构造真正文学空间的理想之光。
三 “至人之迹神其灭”:决绝之焚与惜护之辩
清人文集中多见“焚余”之名[72],相同意义的名称有“烬余”“爨余”“燔余”“焦尾”“焦桐”“爨桐”“焚桐”“拾烬”“萎兰”[73]等,都有烈火余生的意义。既投诸火炬而又未灭,这是一个隐含矛盾又符合一定逻辑的现象。如果还原历史现场,可以寻绎某些特殊事件的脉络,其中所隐含的“应焚”与“不当焚”之辨,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清人的文学标准,以及对既有作品存弃的态度。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先回顾一个清代发生的对大批诗稿本欲“焚毁”而最终“瘗弃”的事件。金匮(今属无锡市)人顾光旭,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为官颇有政声。乾隆四十一年(1776)冬自蜀归乡任东林讲习,在从兄谔斋《梁溪诗钞》和南塘黄可亭《梁溪诗汇》未成稿基础上,复广收故家旧族庋藏遗稿,加以选录编成《梁溪诗钞》。刊刻后对诸稿欲焚欲弃心意未决,最后听从同乡诗人贾崧(字景岳,号素斋)的建议,将“横堆三十尺”的剩稿俱厝土中,立碑其上,名之为“诗冢”。顾光旭特为此事广征诗赋以咏之,随即激起不同反响。
对此举赞同者有之,如赵翼《顾晴沙选梁溪诗成,瘗其旧稿于惠山之麓,立碑亭其上,名曰诗冢,并为赋七古一首》云:“晴沙妙选梁溪诗,二千余年尽罗致。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余残稿将焉置?既非青史蕉园焚,敢托黄册后湖闭。……或笑秦儒将被坑,或疑李集欲投厕。岂知琢石比椁坚,兼复立亭仿塔痉。遂使此邑千才人,诗魂上天魄归地。虽悲一丘貉不分,且喜千腋狐已萃。”[74]袁枚作《诗冢歌》引“本朝顾侠君,选刻元诗三百人”作为审慎甄取的先例,表示赞同,且云:“君今此举古来寡,文冢笔冢难方驾。泥封更比纱笼尊,火烧亦不秦皇怕。我欲高刊华表十丈碑,大书‘过路诗人齐下马’。”[75]
反对的声音也非常强烈,如潘世恩《诗冢歌》云:“文字精灵一点埋不得.熊熊奕奕万丈腾光芒。……晴沙先生选诗一千一百有十人,残编断简堆积高于身。何来贾生出奇计,瘗之石穴千载留其真。君不见,伯鸾不作长康死,名士风流长已矣。”“我思英雄事业才人诗,一例皆欲流传之。选家意见各区别,沧海岂必无珠遗。傥使欂栌杗桷供博采,安在单词只句不与风雅相扶持?”[76]洪亮吉对早年齐名的一些梁溪诗人的作品被埋弃颇有微词:“九原珠玉终难瘗,合置中郎与发丘。”“潘张陆左谁能识?有锸须埋刘伯伦。”[77]同邑秦瀛听闻此事,即作《与顾丈响泉书》直陈其失:“诸家之诗之原本,或锓刻,或钞写,或专集流传,或错见别本,或藏之于其子孙之家,或不必子孙而他人藏之。”他认为:“(《梁溪诗钞》)多者不过一人钞数十首至百首,少且一二首至十数首耳,岂能尽其人之诗而钞之?”[78]张云璈则对贾崧的建议深表不满:“今请一言陈贾公,昔人有诗集曾藏佛寺中。何不将此置之龙光塔,呵护仗彼诸添功?”[79]
梁溪“诗冢”事件反映出清人对文学作品价值的认知,存在着一种带有文化贵族气质的俯视视角,以及一种带有文学劳动者精神的平视视角。前者将最高的文学标准贯穿于选政,却割裂了文学创造的整体脉络;后者则持尊重写作者和文学遗产的态度,认为:“其人一生心血所在,亦应听其自存自亡于天地之间,不应举而弃之土壤也。”[80]综合这两种视角,可以用之解释清人诸多爨弃和焚余现象。
清代“带有文化贵族气质”的焚稿事件,较为典型的是石永宁焚诗。据方苞《二山人传》,永宁,号东村,“世饶于财,祖都图为圣祖亲臣,每议公事,不挠于权贵。山人少豪举,年三十始折节读书。……乾隆元年(1736),举孝廉方正,诣有司力言弱足,难为仪众,莫能夺也”。其作诗“即事抒情,倏然有真意。或刻其《山居》五言律二十首,遂不复为诗,尽焚旧稿。曰:‘吾幼学难补,虽殚心力所造,适至是而止耳。吾幸以悲忧穷蹙,悔曩者之冥行,今老矣,可更以詹詹者扰吾心曲乎?’”[81]此次焚稿,其数量极大,友人闻知后颇赞赏其豪举。李锴《焚诗歌为石东村作》云:“古诗旧说三千篇,未必皆是宣尼删。河清菅蒯颇可诵,春秋交聘犹能宣。逸而不逸谁则主,少者为贵翻争传。石君一旦过我门,道腴义胜来骄人。生平为诗不知数,告我草稿今通焚。丈夫猛捷贵有断,龙蜕不惜黄金鳞。君看《笙诗》无一字,束氏补之成赘文。我闻此论骇卓绝,至人之迹神其灭。”[82]郑夑《寄题东邨焚诗二十八字》更称:“闻说东邨万首诗,一时烧去更无遗。板桥居士重饶舌,诗到烦君并火之。”[83]郑氏非但不以其焚诗为非,更戏谑东村收到自己的诗也可即付诸焚燎。其笔下透出豁达潇洒,给予焚诗者充分的理解:诗乃即兴抒情,无须负载沉重的生命意识,更不必借之传名后世。
文人及其文字业,对一些特定的作者来说,并不能代表身份属性,非生命之追求。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记载:“金陵水月庵僧镜澄能诗,然每成辄焚其稿。檇李吴澹川文溥录其数首,呈随园先生,先生激赏之。吴谓镜澄宜往谒先生。镜澄曰:‘和尚自作诗,不求先生知也。先生自爱和尚诗,非爱和尚也。’”[84]可以看出,镜澄不求袁枚知诗,乃因为诗作出于和尚,而和尚并非以诗荣焉。一旦臻于摆脱世俗尘累的道境,“每成辄焚其稿”则是自然随性的。
东村之猛捷高傲与镜澄之道性自然,有特殊的家族影响和佛门背景,故纵任所作“神其灭”而不及其余,但从普遍性来看,清人还是将文字业看作精神成果与心血存养,焚稿者自身和相关的他者大都以文学劳动者的视角审度和关注,故“焚而有所余”是最为常见的现象。让我们先从“自身”角度试读顺康年间李驎的《楚吟自序》:
李子性嗜吟咏,三日不读古人诗,辄忽忽不自得。九岁即学作诗,然不敢以示人。从父壶庵先生一日于几上见之,李子大惭,先生曰:“子无惭,子可与有成者也。”……戊戌秋,辑前后所作诗刻之,四方作者或以其有合于古人,李子颇自负。久之又自疑,一日读李沧溟集,怃然自失,取所刻诗欲焚之,或止焉,李子曰:“予闻往者七子燕集,于鳞诗必晚出,见他人有工者辄匿己作,自矜其名如此,而集中可删之篇犹且什之六七,吾辈率尔成章辄付剞劂,可谓不自好矣。焚,予犹悔其晚也。”于是遍搜箧笥所存暨所已刻,共得诗一千一百余篇,昼篝一灯座右,稍不自惬辄焚之,仅存篇三百有奇,汇成一集,名曰《楚吟》。……兹所谓“楚吟”,大约皆坎坷困厄之中不得通其意,故发为歌咏,以自抒其愤懑不平之气者。[85]
文章笔意回转,道出千余首诗歌焚毁与甄存的经过和心曲。可见“不自惬”而焚弃之,乃理所当然;将“自抒愤懑不平之气者”留存之,为情之所驱;而“焚余”正是理与情权衡的结果。乾隆时毛振翧自序其《半野居士焚余集》亦称其文乃“自叙其出处,述其言行,备道其所历之境、所值之人、所用之情耳”,故当焚其作品时,不忍心一概弃之,“语从心出,思本性生,其有关于心术人品、气节名义,托物以寄志、藉事以明心者,未始不姑存一二,以对天下后世。不然,此生之所遭逢概湮没而不彰,负身实甚”[86]。嘉庆时刘嗣绾曾叙述陈懋本诗集编集过程曰:“暇日复集其旧时散佚诸作,拨劫后之残灰,拾囊中之碎锦,别为一卷,名曰《爨余》。且以余同游最久,属叙述其梗概。嗟乎!途穷日暮,哀长笛之无多;海碧天青,识断琴之尚在。其能无爨桐之泣、焚砚之思也哉!”[87]不无巧合的是,刘嗣绾《尚絅堂集》卷一所收本人之诗,也以《爨余集》题名。他在卷首叙道:“余年十二三,学为诗,稿脱辄焚弃。岁丁酉,稍稍存录,因就故纸中,并向所记忆者,搜辑一二,名为《爨余》,如曰可入中郎之赏,则吾岂敢。”[88]这样的典型事件表明:清代文人虽宁缺毋滥,平庸辄焚,具有对品质和价值的坚持,但对曾经的精神劳动和心血付出,亦颇自珍[89]。
焚稿虽然是在一定环境和心态下的个人行为,但其现场亦或有亲近者在。站在“他者”的立场,往往当焚稿尚未发生时或爨毁之时力求作挽救性处置,使既成文字精光不灭。陈璞《是汝师斋诗序》记载:
南海朱子襄先生,少负隽才,长励学行,处为纯儒,出作循吏,晚归乡里,设帐授徒,足迹不入城市,平生著述不欲示人,临殁复举其稿尽焚之。此诗一卷,乃其徒窃录出者。沉炼深警,韵高而意厚,何先生犹以为未足传而辄焚之耶?抑其志远且大,以是为小技,而不以贻于后也?[90]
朱次琦,字稚圭,号子襄,世称九江先生。天才卓异,平生史学、理学、文学著述甚富,辞世前尽付一炬,世人痛惜。对于他因何决绝焚稿,门人简朝亮、康有为以及梁启超等皆有评议,大体有愤世嫉俗、不图学者之名、防误读之弊、旧学无益诸说,俱难定论。然而其燔余文字得以传世,毕竟为人间留下散珠碎锦,在文化史上镌刻上一个不朽的名字。其实不但对于清代名人作品,即使对女性或社会底层者的作品,亦有不少救于焚燎的佳话。如郭善邻《张孝子暨妻陈氏行实》记载:“张孝子钊,字宏度,鹿邑人。……先是孝子之将终也,检平生所存诗文一箧,属陈氏曰:‘谨藏,此子长,以相付。’又手一稿草,具涂乙,欲就灯火焚之。
陈氏意其或有用也,为代焚,因易以他纸,而贮稿箧中,且二十年矣。一日,呼其子汉至,启箧,以父命命之,则向所欲焚稿者固在。语之故,汉受而读之,乃吁天文也。”[91]陈氏的行为未必出于文化自觉,但在朴素的直接经验驱使下,家族文学之光得以鉴照后人。
与从火炬中挽救残篇相比,乾隆朝周广业对所作《宋六陵考》“欲焚稿者数矣。顾念搜讨之劳,颇费时日。又窃喜扣盘之见,间有与先哲隐合者,遂未忍割弃”[92];道光间贝青乔“屡欲焚弃”往日书文,终因“朋好中有劝其存稿”[93]而从之;晚清罗振玉“间作小文,不欲再存稿,儿孙辈顾以为可惜,编成一卷”,振玉便“署其端曰《未焚稿》”[94]。这种事前终止焚稿的行为不乏记载,其中有自我心灵的对话,也有与他者的对话,从中能够感到人们对将文字归于回禄之神所持的慎重态度。
四 清人焚稿的几个新特点
焚稿,是一种阻断作品传播的手段,从社会意识角度看,具有抗拒社会的意向和控制个人损害的作用;从文学的角度看,则是一种特殊的、严格的自我批评方式。这种批评方式受到唐代以前删诗、焚书、烧砚、焚谏草等文化事件的影响,唐宋文人层出不穷的焚稿行为赋予其典型意义,至明代已经发展为一种文化风尚了。清人焚稿不但集历代之大成,而且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趋向和特点。
首先,焚稿作为士林风俗更加普遍流行。至迟到唐代,文人中已经出现了“祭诗”行为,乾隆年间鲍倚云有《祭诗行》云:“我闻祭诗之例贾岛开,时当除夕陈樽罍。命意还应自劳苦,亦或艰辛历历如有神助灵之来。……玉堂老人(东皋伯父)顾之浩然叹。问我试啼英物如何英,而不思吹龙笛与凤笙。快剑入海屠长鲸,为我掷地作石声。何为效此蚓泣苍蝇鸣,积数百篇悉焚弃。”[95]实际上唐代“除夕陈樽罍”而祭诗只是滥觞,至宋代方逐渐演变为一种风俗。弘治《八闽通志》记载:“闽俗相传,谓腊月二十四日,灶君上天,奏人间事,必祭而送之。(郑)性之贫时,尝于是日贷肉于巷口屠者之妻。屠者归,闻之大怒,径入其舍,索其肉以归。性之乃画一马,题诗其上,焚以祀灶云:‘一匹乌骓一只鞭,送君骑去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96]至清代,祭诗已发展为士林和民间普遍流行的习俗了,“酹酒焚诗以哭之”[97],“醵饮陪三爵,焚诗代纸钱”[98]成为寄哀仪典的程序,而送腊及除夕焚诗更每见于诗人笔下。
张问陶《甲寅京师送灶》:
司命居然醉,焚诗与送行。
报功惟饮食,举火即神明。
小象厨人媚,余饧稚子争。
素餐归未得,风雪故乡情。[99]
法若真《七十一自寿二十首》(其六):
柴门落落问谁关,一任牛羊自往还。
绕屋长悬双涧水,当轩不去两珠山。
经年检药余铛在,送腊焚诗信笔删。
多病于今将四载,犹消花径老闲闲。[100]
宗智《除夕同盛子嘉限除字》:
风雨催残腊,高眠任岁除。
寻梅双屐静,留客一樽虚。
检箧焚诗草,挑灯阅道书。
飘蓬同十载,赢得鬓毛疏。[101]
显然,焚稿至清代已经高度仪式化、信念化了。岁末是焚稿仪式最隆重的时刻,人们在检箧删诗中谛视创作过程,升华审美意识;这也是举行拜祭的时刻,在燎烟中将对文学的信念熏染于日用常道,人们期待“祭诗尚可搜残帙”,“鹊噪晴檐报好音”[102],从而展开新生活的一页。
其次,焚诗成为文学旨趣转移和文体变更改辙的突出标志。清人在文体间弃故开新,如果要建立一个界标,通常以焚稿作为宣告。朱彝尊为倪我端所作墓志铭记载:“同里倪君,识之四十年,君时授徒城东竹亭桥。即其人,恂恂有君子之容;观其文,悉本经义。君早见知于有司,九试场屋不利,年四十八以岁贡入国子监。诸城李侍读澄中读其廷试卷,亟荐之。榜发,以儒学训导待铨。是秋赴顺天乡试,复不遇。君乃焚所作诗文,就予宣南坊邸舍讲经义,学为古文辞。”[103]金武祥《蒋君鹿潭传》载有蒋春霖焚弃诗稿专意为词的事迹:
君故力于诗,追源究流,靡不洞贯,积稿累数寸,中岁乃悉摧烧之,语所知曰:“吾能诗非难,特穷老尽气,无以蕲胜于古人之外,作者众矣,吾宁别取径焉!”用是一意于词,以终其身,然亦卒成大名,晚年删存诗,仅数十篇。[104]
蒋氏业诗“积稿累数寸”,可见用功之深、创作之富,然而“好为诗”未必能成名传世,若置于庞大的作者阵容中不能木秀于林,还另取他径。清代词学中兴的原因较为复杂,部分文人弃诗入词,虽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文人群体性情之变的某种动向亦值得注意。
再次,焚稿进入写作题材,出现了抒情色彩浓厚的文学作品。焚稿作为与创作具有紧密关联的文人活动,很早就成为叙事、描写、抒情的内容,大量的燔余序可以看作较为专门的焚稿文,但清代以前这类写作往往重事轻情,以交待文本之所以“焚”与“余”为主。而清代如鲍倚云《祭诗行》等大量篇章,叙事成分弱化,抒情色彩有所增强。更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朝出现了汪绂《焚稿文》这样的专题性作品。
该文叙述,“新安汪绂于丙申、丁酉二年之间,因道路流离,心无俚藉,每寓言托物,以舒离忧,多所著作,而未轨于道。有时文数百篇、杂诗百余首、杂文数十百首,中有圈者、点者、丶者、读者、句者、抹者、涂者、乙者、真者、草者、前后不相接续者,卷帙散乱,堆塞满笈”,故欲付之爨毁,虽受到劝阻,仍“发笈陈稿,焚之于西阶之上”[105]。虽以作者之名发端,但其后只有“先生”与“门人”的简短对话,作为焚稿情节发展的脉络,而“为文而祭”的内容在全文占有主要篇幅,文字典雅,抒情色彩浓郁,爨燎心绪层层道来,动人心魄。
这表明,焚稿事件在清代文人谱系中占有了一定位置,不仅具有客观记录的必要,而且作为生活众相的一个侧面,具有了成为文学作品题材的典型意义。这类作品不但可以填补清代文人履迹,对古代文献史料学、古代文人生活与创作心态研究有参考价值,其文本作为抒情作品亦不乏审美功能。
五 余 论
胡塞尔认为凭借“直观”对我们所意识到的“意向对象”加以描述,即“现象学还原”,这种还原不仅要“回到事情本身”,还应当追问直接的体验和直观之中的“本质结构”[106]。大量文献记载以及黛玉焚诗葬花的凄美故事,使清代焚稿问题早就进入了学术界视野,但相关研究,特别是对焚稿现象“本质结构”的分析尚远远不够。由于焚稿具有一定的隐私性,许多事件的缘由和真相还被遮蔽着,有待考索发覆。在此基础上,对焚稿这种受社会意识支配和受文学价值观影响的行为的“本质结构”才能够得到深入的揭示。
当然与之联系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前人焚稿所形成的文化惯习,包括史学等学术著述的焚燎对清人的范例作用到底如何;不同时期的政治力量导致的焚书毁板对清人焚稿心理产生的影响如何;清代文学创作重心下移及其日用性、通俗性、娱乐性的写作方式与焚稿行为的内在联系如何;对于不同文体,清人的焚弃态度和表现强度有无差别;作为一种特殊的批评方法,其焚与弃的选择尺度是否体现出清人独特的文学观念;焚余锦灰对文人个体和清代文学、文化史的特殊价值是什么;焚稿仪式在社会学和文学视野中具有何种不同的行为艺术作用;焚稿过程是否包含欲扬先抑的动机和潜寓传名的意图;各社会阶层的女性作家焚稿有何心理差异;纳入跨文化比较题材来看,中外作家焚稿意识和行为异同之处在哪里?这些都是可以专门探讨的话题。更为重要的是,焚稿对作家个人是否具有纯化心智、救赎精神、提高文品的效用,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可以看作有益的淘汰机制呢?置于清代学术史和文学史,又应该如何辩证分析这一行为带来的作品大幅减少的事实?
这些问题比较复杂,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如果将清人一系列焚稿事件结合起来的话,已不失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叙事,能够唤起研究者发现其与历史的联系——不仅寻求某些具体史实的存在,而且探求史实背后的意义。如此,对文学现象的还原,能够体现出对历史还原的努力。
本文原载《文学遗产》2017年5期
感谢罗时进老师赐稿!
参考文献
[①] 周亮工焚书时间,一说为康熙九年(1670),陈圣宇《周亮工晚年焚书日期确考》考为康熙十年二月初五,参见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古典文献研究》(第11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541—544页。
[②] 吕留良《吕晚村文集》卷五《栎园焚余序》,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339—340页。
[③] 陈鼎《留溪外传》卷四《吕晩村传》,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自刻本,第22b页。
[④] 屈大均《明四朝成仁录》卷一二,民国影印《广东丛书》本,第448b页。
[⑤] 何绍基《(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二六〇,清光绪四年(1878)刻本,第3b页。
[⑥] 阮元《两浙輶轩录补遗》卷一,清嘉庆间刻本,第14a页。
[⑦] 侯方域著,何法周主编,王树林校笺《侯方域集校笺》卷二《曼翁诗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第63页。
[⑧] 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二八《彭燕又偶存草序》,《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版,集部第352册,第131页。按,吴伟业本人居京师时曾“岁抄日记,有成帙矣”“藏在箧衍,不以示人”,后“恐招忌而速祸,则尽取而焚之”(《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18页)。
[⑨] 傅山《霜红龛集》卷三七《杂记二》,《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5册,第497页。
[⑩] 张升《王铎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页。
[11] 蒋良骐《东华录》卷二一,清乾隆间刻本,第22a—22b页。
[12] 任如松《四库全书答问》,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2页。
[13] 颜元《存人编》卷二《唤迷途·第五唤》,《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上册,第146页。
[14] 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上海书店2007年版,第165页。
[15] 徐崧《凡例》,徐崧、汪文桢、汪森辑《诗风初集》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56册,第632页。
[16] 钱陆灿《赖古堂集附录·墓志铭》,周亮工《赖古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下册,第946页。
[17] 吕留良《赖古堂集序》,《赖古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下册,第553页。
[18]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七三,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4册,第355页。
[19] 余绍宋《梁节庵先生诗集序》,《余绍宋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31页。
[20] 钱维城《钱文敏公全集·茶山文钞》卷一二《朝议大夫分巡南汝光道布政使司参议永济崔公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3册,第90页。
[21] 张问陶《船山诗草》卷一五《闻稚存赦归先寄》,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册,第430页。
[22] 李天植《李介节先生全集·蜃园诗后集》卷三《次答叶香上》,《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7辑第19册,第505页。
[23] 李驎《虬峰文集》卷一六《许君平先生小传》,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第34a页。
[24] 张问陶《船山诗草》卷一七《闲中得句》,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册,第509页。
[25] 吴绛雪《徐烈妇诗钞》卷一《招素闻以诗代柬》,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二编》,黄山书社2010年版,上册,第27页。
[26]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5页。
[27]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28] 骆绮兰《听秋轩闺中同人集序》,《江南女性别集二编》,黄山书社2010年版,上册,第695页。
[29] 夏伊兰《吟红阁诗钞·偶成》,蔡殿齐编《国朝闺阁诗钞》(第九册)卷三,清道光二十四年(1848)嫏嬛别馆刻本,第3a页。
[30] 这里说“主要归宿”,是指清代女性希望刊刻诗作,流传作品的现象有所存在,这方面的事例参见严程《清代女性诗人的联吟唱和与存稿情况例说》,《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31]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二七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册,第2137页。
[32] 参见拙文《焚稿烟燎中的明代文学影像》,《苏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33] 沈立东《中国历代女作家传》,中国妇女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34] 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卷四《汤母杨太淑人吟钗图记》,《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9册,第165页。
[35] 顾贞立《焚旧稿》,完颜恽珠《国朝闺秀正始续集》卷二,清道光十三年(1833)红香馆刻本,第14a页。
[36] 沈德潜选编《清诗别裁集》卷三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64页。
[37] 郭善邻《春山先生文集》卷三《张母刘夫人行实》,《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9辑第26册,第353页。
[38] 黄秩模编,付琼校补《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校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2页。
[39] 关于清人罢官之际的焚稿,每见记载。如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六:“陈顾?,字又声,亦作牖声,号藕田,仁和人,乾隆乙丑进士,官户科给事中。……所著有《南楼文稿》《续稿》《诗稿》若干卷,罢官日悉自焚弃,所存《北梁吟稿》皆在塞垣时作也。”(《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5册,第170页)
[40] 参见胡传志《日课一诗论》,《文学遗产》2015年第1期。
[41] 参见蒋寅《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
[42] 刘绎《笃志堂古文存稿序》,上官涛、胡迎建编注《近代江西文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
[43] 毛奇龄《西河文集·序》卷一〇《吴应辰诗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7册,第267页。
[44] 汪懋麟《雄雉斋选集序》,顾图河《雄雉斋选集》,《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册,第345页。
[45] 张贞《渠亭山人半部稿·潜州集》《诰授奉政大夫礼部仪制清吏司郎中曹公贞吉墓志并铭》,清康熙间安丘张氏家刻雍正印本,第66a页。
[46] 曹贞吉《珂雪初集》卷一《岁暮感旧抒怀二十八韵》,《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册,第240页。
[47] 范锴《浔溪纪事诗》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80册,第297页。
[48] 张龙辅《玉狮坠·序》,《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3册,第1681—1682页。
[49] 史澄《(光绪)广州府志》卷一二八,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第19b页。
[50] 汪淇《与关蕉鹿》,黄容、王维翰辑《尺牍兰言》卷四,《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集部第35册,第213页。
[51] 邵晋涵《南江诗文钞》文钞卷八《与吴百药侍读书》,清道光十二年(1832)胡敬刻本,第2a页。
[52] 王甥植《茗韵轩遗诗·雨后书事》,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四编》,黄山书社2014年版,下册,第1005页。
[53] 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95-496页。
[54] 贺铸《庆湖遗老诗集》自序,《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3册,第197页。
[55] 参见[日]浅见洋二著,朱刚译《“焚弃”与“改定”——论宋代别集的编纂或定本的制定》,《中国韵文学刊》2007年第3期。关于徐府焚少作事,参见楼钥《萝林居士文集序》引向士諲为徐俯诗集所作序文:“公为徐东湖诗集后序有云:‘始为诗以数百计,一见师川快说诗病,尽焚其稿。’则知公之少作尤多,其所存者止此耳。”(楼钥《攻媿集》卷五二,《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011册,第713页)
[56] 先著《之溪老生集》卷二《严许集下·焚诗》,《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8辑第28册,第483页。
[57] 李伍渶《壑云篇文集》卷二《郑慎子诗叙》,《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册,第526页。《壑云篇文集》卷二《史评小引》又云:“某二十许时,无所知识,妄为史论,褒讥千古,震憾河岳,不顾膑绝而压覆以死也,一旦感杨诚斋《柳》诗而悔之,尽焚所为史论二百余篇,三十年阁笔不敢臧否人物。”(《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册,第529页)
[58] 章藻功《思绮堂文集》卷三《汪无己焚余诗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册,第495页。
[59] 方东树《半字集》《半字集序录》,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07册,第1页。
[60] 周篆《草亭先生集·诗集》卷二《戏题焚剩诗稿》,《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6册,第501页。
[61] 张煌言《张苍水集》第一编《陈文生未焚草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5—46页。
[62] 薛雪《一瓢诗话》,叶燮、薛雪、沈德潜著《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页。
[63] 李嶟瑞《后圃编年稿》卷首《焚余稿自序》,清康熙间刻本,第5a—5b页。
[64] 薛雪《一瓢诗话》,叶燮、薛雪、沈德潜著《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页。
[65] 林昌彝著,王镇远、林虞生标点《林昌彝诗文集》卷一四《林子莱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页。
[66] 典型的事例是康熙初“海内以诗名者推士祯,以文名者推汪琬。而嘉兴叶燮,字星期,其论文亦与琬不合,往复论难,互讥嘲焉。及琬殁,慨然曰:‘吾失一诤友矣!今谁复弹吾文者?’取向所短汪者悉焚之”。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八四《文苑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4册,第13364页。
[67] 清人唐宋诗之争,在学界讨论中似有泛化倾向,实际上正如袁枚在评论唐宋诗风的时候说道:“夫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子之胸中已有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册,第1506页)沈谨学《简徐冶伯晋镕即题诗稿后》的评论亦富于见识,他说:“想见连番得意吟,论工数拙岂初心?浪分格调或唐宋,毕竟性情无古今。”(沈谨学著,马卫中、陈国安点校《沈四山人诗录》,《贝青乔集》外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页)关于焚稿问题,孔尚任序李嶟瑞《焚余稿》曰:“吾得李子苍存《焚余稿》,逢人说之,谓其不让古人,必传无疑。闻者诘曰:汉乎?魏乎?唐与宋乎?余曰:古人皆无此家格,但能使读者如见作者之性情,如获自己之性情,是即自成一家格。”(刘辉《所见孔尚任诗文二题》,《文献》1985年第1期)此说最为通达。
[68] 陆继辂《崇百药斋文集》卷一九《候补觉罗官学教习钱君行状》,《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06册,第226页。
[69] 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0册,第174页。
[70] 单学傅《海虞诗话》卷九,《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6册,第65页。
[71] 冯志沂《适适斋文集》卷一《送余小颇先生出守雅州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39册,第642页。
[72] 遭劫火而幸存的别集,一般以“劫灰”“然灰”为名,与“焚余”的意义有所不同。
[73] 胡文楷编著《历代妇女著作考》:“(王如沂妻)年二十五,夫殁,尽焚所作诗,守节二十年卒,子侄等捡箧得残稿一卷,题曰《萎兰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35页)
[74] 赵翼著,华夫主编《赵翼诗编年全集》卷三九《顾晴沙选梁溪诗成,瘗其旧稿于惠山之麓,立碑亭其上,名曰诗冢,并为赋七古一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册,第1224页。
[75]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诗集》卷三六《诗冢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册,第1044页。
[76]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〇九,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3册,第140页。
[77] 洪亮吉《卷施阁集》诗集卷一八《诗冢诗》,《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7册,第632页。按,此诗有序,述作诗之由:“无锡顾兵备光旭选刻同县人诗为一集,其剩稿贾上舍崧乞得之,为卜地瘗于梁溪之侧。三伏日走数千里为索诗,可云好事矣,爰为赋四绝句。”
[78] 秦瀛《小岘山人诗文集·文集》卷二《与顾丈响泉书》,《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07册,第469页。
[79]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九四,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2册,第667页。
[80] 秦瀛《小岘山人诗文集·文集》卷二《与顾丈响泉书》,《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07册,第469页。
[81] 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八《二山人传》,《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0册,第394—395页。
[82] 铁保辑,赵志辉校点补《熙朝雅颂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2页。
[83] 郑夑《板桥集》二编《寄题东邨焚诗二十八字》,《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3册,第635页。
[84] 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清道光十七年(1837)振绮堂刻本,第7a页。
[85] 李驎《虬峰文集》卷一五《楚吟自序》,清康熙刻本,第15a—16a页。
[86] 毛振翧《半野居士焚余集》自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册,第578页。
[87] 刘嗣绾《尚絅堂文集》卷二《陈季驯诗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69册,第417页。
[88] 刘嗣绾《尚絅堂诗集》卷一《爨余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69册,第122页。
[89] 清人还有因绝嗣或平生无名而决绝地焚毁全部作品,毫不惜护的,如俞蛟《梦厂杂著》卷一《李少白传》(清刻深柳读书堂印本)说嘉道间李少白临殁前将“半生怵心刿目而为之”的篇什付之一炬,不作任何选存,即出于对绝嗣的极度悲哀。清初秦卫周“愤其诗无知者”,尝“搜其(诗)若干卷,大饮哭曰:‘恨唐人不见秦生,天生秦生何为耶’”,并焚弃其稿,参见王铎《拟山园选集》卷四五《秦兰亭李虚衷传》,《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册,第191页。这些都属于极为特殊的个案。
[90] 陈璞《尺冈草堂遗集》卷一《是汝师斋诗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76册,第649页。
[91] 郭善邻《春山先生文集》卷三《张孝子暨妻陈氏行实》,《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9辑第26册,第351页。
[92] 周广业著,祝鸿熹、王国珍点校《周广业笔记四种》,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
[93] 齐思和、林树惠等编,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三册,第233页。
[94] 罗振玉《罗振玉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页。
[95]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九七,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2册,第729页。
[96] 陈道《八闽通志》卷一三,明弘治间刻本,第23b页。
[97] 詹应甲《赐绮堂集》卷六《宿吕堰驿吊王巡检二首有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65册,第297页。
[98] 李继圣《寻古斋诗文集·诗集》卷一《冀署诸友邀徃郊外设筵迎喜神口号》,《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集部第168册,第353页。
[99] 张问陶《船山诗草》卷十一《甲寅京师送灶》,中华书局1986年版,上册,第304页。
[100] 法若真《黄山诗留》卷九《七十一自寿二十首》(其六),《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4册,第282页。
[101]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九七,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4册,第859页。
[102] 方焘《山子诗钞》卷七《除夕感怀四首》(其四),《丛书集成续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76册,第357页。
[103]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七八《儒学训导倪君墓志铭》,《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册,第580页。
[104] 蒋春霖著,刘勇刚笺注《水云楼诗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29页。
[105] 汪绂《双池文集》卷七《焚稿文》,《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1册,第662—663页。
[106] 参见邓晓芒《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学还原》,《哲学研究》2016年第6期。
学 衡
【学衡】微刊由北大、社科院学人发起,国内数所高校师生参与运营。意在承续民国《学衡》杂志“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之宗旨,秉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之主张,介绍、反思古今中外之学术,分享新的知见与思考。文章力求内容原创、思维敏锐、文字雅洁,栏目涉及学术、学人、文艺、时评等等。《礼记》言:“合志同方,营道同术”,愿海内有同志者助我臂力,共襄盛举。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欢迎与朋友分享!阅读更多原创文章,请关注【学衡】微信公共平台!我们也一如既往地期待您和我们分享您的意见、文章和智慧!投稿信箱为【xueheng1922@126.com】转载请与本刊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