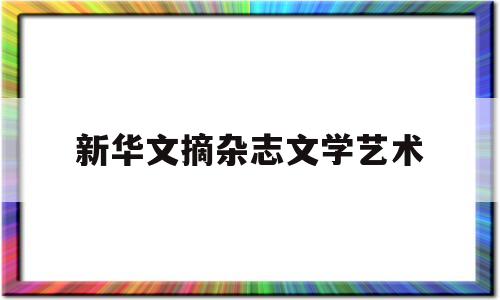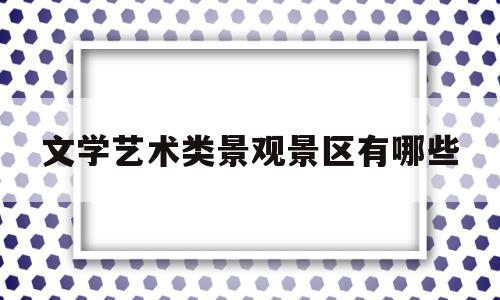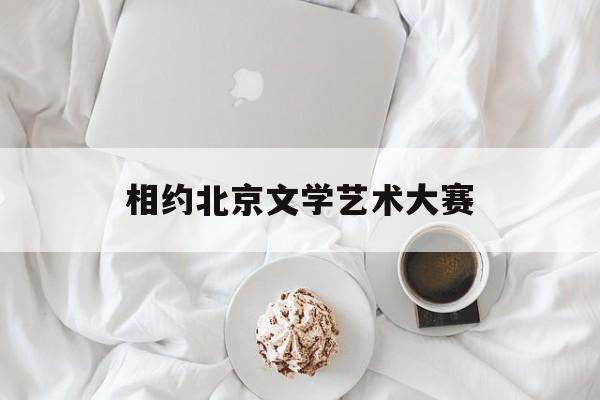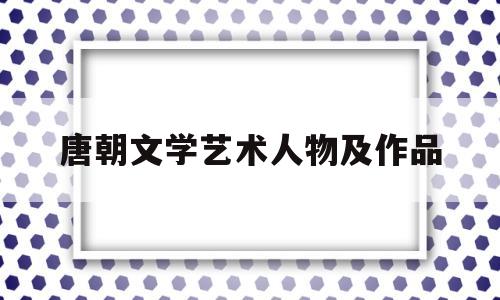每年得读读《诗刊》与《诗选刊》,几乎是每期全部都要读的,除非借阅时借漏了。今年,多去怀化学院借书。上半年去了一次怀化市图书馆,除了借阅上半年的《读书》和部分《新华文摘》,便是借阅了上半年的《诗刊》。
去怀化图书馆的好处,一是借阅杂志,二是新书比怀化学院上架快。杂志时常是养肥了,再借。这几年去怀化图书馆借阅杂志,连工作人员也说,愿意借给我。说我是坚持不懈的借阅者。前几年,没人去借阅杂志,只我一人。开始,工作人员说,没有先例,不好答应。我找了一个管业务的馆长,交了一百元押金,开了先河。如今,以前每次限借十本。后来,我守信,读得快,又能按时还回来,答应每次借阅十五本。几年下来,大致已经借阅了几百本了。开始,一个登记借阅的本子,所记的半本,只我一个人登记。几年下来,说是后来也有零星的人借阅了。可工作人员说,所来的几个,多只借阅了一两次,便不再来了。其中一个,只借阅《围棋天地》,来了几次,现也不再来了。我是围棋爱好者,围棋也是诗,只是如今年岁来了,已经跟不上围棋诗意的趟了。围棋高手,只要学做诗,我想一定会成为诗园高手。
读完了2017年《诗选刊》1月号和2月号上半月两本,只能说我的这个老丁丁的欣赏水平,如同我的围棋水平跟不上《围棋天地》一样,不能与时俱进了。可能是不能引起共鸣,两本刊物,读得很快。要说读得不认真,自己也不认帐,是每首诗都扫过了的。
两本《诗选刊》中,最喜欢的是2月号中的一道,回神再看作者,余秀华的。读《诗刊》与《诗选刊》,我不看作者。凡遇到喜欢的诗,再去看作者。以前在《诗刊》上读过几首特别好的诗,是戴潍娜的。这个人,便记住了。今后,她的诗,或是她的诗集,定然是要好好读的。这人的文章,后来在《读书》和《新华文摘》中见了(印象是这两本刊物),她的文字,与她的诗比较,力道有过之而无不及。读两本《诗选刊》,能够很快的在扫读中,发现我喜欢余秀华的诗,可见,喜欢她的诗,还真不假。称得上,众里挑她千百度。
诗,需要翻转跳跃,不光光是情感的,必须有直白裸体的灵闪,这样才能真正打动人。余秀华,具备这样的诗质。这首诗不在她的集子里,录下来,算作笔记。
《悲伤无法成诗》
余秀华
“肿瘤医院的一块休息区树木高大/两个人才能围抱。树荫整日浓稠/鸟鸣透不下来/我面前的石桌裂了几条缝,盯着看/能把人陷进去/妈妈在不远的地方和人聊天/她的头发还在,又长又黑/这时一只鸟掉下来,落在我的面前的石桌上/它的眼神清澈得让人世绝望三次/我不敢让这人间悲伤/被它衔到树梢,带到天上。”
不夸张的说,两本《诗选刊》能读到余秀华的这一首诗,足矣!好多《诗选刊》的诗,好句子,不能连读下去。翻转跳跃,也莫名其妙!有些好诗句,单提出来,感受挺好。放到诗中,只一处打眼。从诗的立意而言,也有较好创意的,特别是在推出的“新诗别裁”这个栏目。可叫人总体的喜欢上一首完整的诗,不大容易找。两本《诗选刊》,我的读感,这诗要么写得太漂浮,要么写得太自我,要么缺少学养与思想沉淀,要么不是诗人强作诗。
在朋友的推介下,我关注过很长一段时间《颓荡》与《颓荡写作》,这是一任个性张扬的诗园地。如今,其中一个可能是因为“黄”与“性”的问题,关闭了。还有一个,到现在还是间断的发些诗。所发出来的诗,不时的也因为内容问题,被删除。《颓荡》与《颓荡写作》,是个退到人性根上的发问性质的创作,好些作者放弃了自身符号意义,行走地“性”的“核心”地带,周游玩耍在“我到底需要什么?”“我与周边的人与事是个什么关系?”“我怎样才是我?”等一系列的追问中,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良莠各现,参差不齐。不过,真的有好些振聋发聩的好作品,叫人垂怜,叫人刮目,叫人共鸣,让人叫绝。有一点,是共同的,全部的创作,归根在“性”出真知!
之所以用《颓荡》与《颓荡写作》来说说诗,是因为我们的诗,有种被捆绑飞翔的总体态势,太放不开。而《颓荡》与《颓荡写作》,又对常人而言,放得太开。我们能够公开发表的诗,要不是对诗的理解,太逼仄;要不是对诗的态度,太随便。好些的人,对待诗,以为只要用文字,间断的真实的表现出自己的情感与志趣,便是诗了。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对于新诗而言,只要有字,便可称诗。而从总体上说,好的诗,是要有人类关怀和个人关怀表现与追问的。简单的说,诗是智慧的琴瑟,需要的唱和,需要和鸣。
为了说明这个观点。用2017年《诗选刊》封二的黄永玉的《老头还乡》说事:
“杜鹃在远山的雨里/墙外石板路上响着屐声。/万里外回到自己幽暗的木屋,/杏花香随着从窗格子爬进来/刚坐下来就想着几时还能再来。/理理残鬓,/七十多岁的人回到老屋,总以为自己还小。”
黄老的这首诗,实在是平实得不能再平实。没有太多的翻转跳跃,也没有太多尽义的玄思妙想。可这首用黄老手体字刊出的《老头还乡》,当是公认的一首上好的诗。为什么?
一是此时此地,此人此景的真实(这点多数人能够做到);
二是离开了表现手法追求,自然写照白描勾勒的真实(这点好多人不容易做到);
三是写出人人意中有,只有功力到堂人才能勾勒出恰到好处“速写”与“写生”的意境(心此自然的境界)。
“杜鹃在远山的雨里”,即景即情,带点遥望家乡的铺垫。
“墙外石板路上响着屐声”,追忆听昨,带上了点“跳跃”感,与距离和时空感的陡然的浓缩。
“万里外回到自己幽暗的木屋”,现实存在感的强化,带上现实老旧与外在变化对比,同时牵引出思乡的缕缕情愫。
“杏花香味随着从窗外格子爬进来”,杏花香味,在发散了,叫人遐想,叫人疑问,叫人异地周置,现实的香味中,带上了不尽义的联想,其中那些暗指与翩联,只有作者自己才能知道。但读诗的时候,作者的心思,也好像是我们自己的心思。这里便有开始了共鸣!
“刚坐下来就想着几时还能再来”,这便是笔道与力道了。没有刻意的追求,只在千言万语中,选出这么的一句,正如画画的那一笔,那一触,不偏不倚,不重不轻,刚刚的好。老当将老,回可还回?
“理理残鬓,七十多岁的人回到老屋,总以为自己还小。”这句,是这首诗根性上的表达,表现岁月,表现人生,表现乡情。从个人关怀(我的老,与我的思乡之情)引带出人类关怀(是人皆老,人之乡情),质朴几句,带着童真与人的本真,玩趣十足。
诗的另一种被捆绑的表现,有种被鞭赶的方向性。没有想表达的,非得去表达,为了表达而表达,这是其中一种;有了强烈的表达,非得朝向老师或书本规范的指向,或者必须按照某个的硬性调子走,这是另一种。还有一种捆绑,是头重脚轻,什么想法都有,愿望极其的好,可是平日里积累太少,飞不起来。正好相反的一种,脚重头轻,基础非常好,底子也厚,就是少了飞起来灵感和形象思维的翅膀。
还是那句话,诗,人人可以写,也人人写得几句自鸣得意的诗。但诗要成为大家认为好诗,能够引起强烈的共鸣,不是随意可以做到的。
说回余秀华上面这道《悲伤无法成诗》诗。全部的诗句,与悲伤有关,可细品诗句,的确情境体察不出什么太多直接的悲伤。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在那些诗句中的“肿瘤”、“医院”、“树木”、“树荫”、“鸟”、“我”、“石桌”、“缝”、“人”、“妈妈”、“头发”、“天上”等符号,再加上动词与形容词的间插,你可以感受两个人才能围抱下来树与人之间,生命力现实与渴望; 生命力与肿瘤医院之间的反差;可以感受鸟鸣外面自由世界,与树荫下浓稠下丧失了健康自由的隔膜;可以感受石桌缝把人陷下去,魔幻出又黑又长的希望;可以感受“我不敢”“人间悲伤”“带到天上”的断意间,无限的畅想。她的诗意下,潜伏的是有意无意间,深深的沉思,还有淡淡的无奈。
诗,是播撒。是心田中,理想之乡,那飞扬的梦中柳絮。
2017年10月15日清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