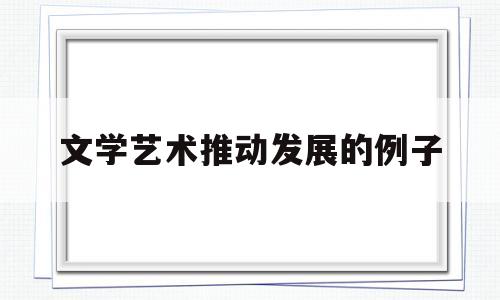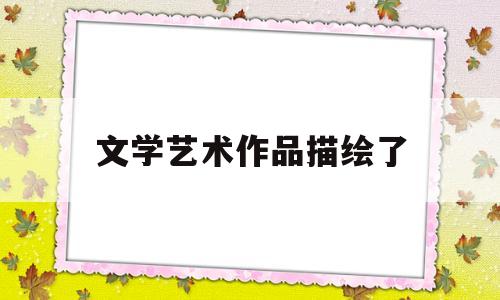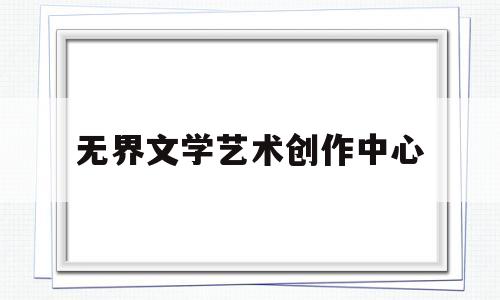法国新浪潮电影旗手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半自传性质的代表作《四百击》不仅让特吕弗一举成名,更使得《四百击》成为了法国新浪潮电影史、乃至当代世界电影史上的一个标杆。时至电影放映四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重温这部经典时,作为一个身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环境的观众,与电影放映时的观众相比,我们或许能从一个旁观者、局外人、“异文化的感受者”的角度来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社会与一些相关的文化现象。同时,由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现代性”生长的关键时期和“后现代主义”萌生、发展的重要时期,《四百击》这部充分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社会现状及其新思潮、新现象的电影,也使得我们能从历史、文化、社会的角度进行思考,去解读一些有关“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与现象。
首先,在题材方面,《四百击》以青少年为“真正主角”,并以写实主义的原则深刻剖析青少年及其与家庭、社会的互动关系,这在根本上体现出一种对青少年在电影乃至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的新认识与新的定位。
正如特吕弗自己在《关于孩子与电影的思考》中所说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相比之下,他们在电影作品中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当然也有一些电影中出现了孩子的身影,但真正以孩子为主题的作品却微乎其微。……从商业角度看,电影以展示明星为本,孩子的出场纯属多余,他们身处情节之外,往往只是装饰或点缀。”特吕弗特别强调,在塑造孩子的形象时,要“不仅拍摄孩子的游戏,还记录他们的悲伤,那些与成人间的冲突毫不相干的巨大悲伤,那么作品就能达到更大的真实。”
特吕弗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罗塞里尼、维托里奥·德·西卡等将儿童的天真纯洁与成人的腐化堕落形成强烈对比的表现手法不同,他以平心静气的、客观的视角看待童年,着力强调的是天真和儿童机灵的反面。正如影片最后安东万与心理医生的对话所显示的那样,儿童的世界不像成人的世界那样乌烟瘴气,但青少年追求逃脱,却又可能受成人世界的影响而走上腐化、玩世不恭的危险道路,过早沾染一些坏习气。在少管所,安东万与心理医生的那段对话中,医生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来评估少年的困境,安东万谈论自己的这一段场景,特吕弗创造性地采取了跳切技巧,让人印象深刻,似乎这个孩子就是在以回答这一个个的具体问题的方式来向人们展示一个个少年问题的具体案例,供观众分析。由于采用了正面拍摄手法,所以安东万的脸是正对观众的,而心理医生则是背对观众的,问话则以画外音的形式传来,使得这种问答的“案例展示性”格外浓厚。尽管在剪辑后,这段对话的先后事件并不是很有条理很连贯,却在展现安东万的性格方面增添了极其人性化的一面。
的确,在特吕弗写实主义的镜头里,“真实的”孩子并非像成年人想象的那样是天真无邪与纯洁的代名词,孩子们、尤其是“8到15岁的”、正处于“意识觉醒的年纪”和“青春前奏”的孩子们是叛逆不安的,他们会严肃地思考,也会沾染上一些成人世界的习气的,渴望尽快长大、融入成人社会却又始终在抗拒着成人社会的规则。特吕弗说,“与青春携手而来的是对不公正的发现和对独立的渴求,是情感的断奶以及对性的朦胧的好奇。因此,这是一个关键的年纪,是绝对道德与成人的相对道德之间,是心灵的纯洁与不洁之间开始发生冲突的年纪,这也是任何一位艺术家都认为最值得他们挖掘的年纪。”“青春期这一阶段向来得到教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承认,却遭到家庭和父母的否定。套用一下专业术语,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情感断奶,生理唤醒,独立欲望与自卑情结。稍有情绪波动就会叛逆反抗,这种症状被称为‘青春期自立危机’。世界是不公平的,必须比寻出路,于是青少年就借助胡作非为(‘四百击’)来表达他们的强烈抗议。”所以,他“决定把青少年时代描绘成‘一段艰难的时光’,而不是大多数人眼中的温柔怀旧。”因为唯有这样,孩子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饱满的、深刻而细腻的“主角”,而不再仅仅是点缀、或者是唤醒观众童年记忆与感动的道具。
可以说,《四百击》就是特吕弗带着这种新观念、新认识进行儿童电影创作实践的一个典型而成功的案例,《四百击》的主人公安东万就是一个处于这种“青春期自立危机”之中的、非常复杂的青少年形象,他基本上是一个“问题少年”,完全不符合人们传统印象中天真无邪的孩子的形象——他淘气、不遵守纪律、逃课、伪造假条、用妈妈死了来谎编逃学理由、渴望摆脱父母独立生活、经常撒谎、偷东西、甚至差点召妓;另一方面,他也尽力地多做一些家务,大部分时间都比较听话,渴望出外谋生养活自己,迷恋巴尔扎克,努力地想要写好作文,在被冤枉、受到不公正待遇后会很气愤,在偷了打字机后很快又后悔决定再送回去。可见,安东万是个渴望自由、叛逆乖张的孩子,但他也会尽力地去符合社会的要求、迫切想要融入成人的世界。
就像特吕弗说的那样,他“不会区分意外与过错”,在他看来,逃学和偷东西不会有太本质的区分。因此,特吕弗指出,“根据这些小故事,就能拍出一部电影,这也说明一步儿童电影完全可以由‘小事件’组成,因为,事实上,孩子的世界里没有‘小’事。”从这点来看,《四百击》虽然有较为清晰的整体故事脉络,但却基本上是由一连串的“小事”串成的,而且其中穿插着大量信息丰富的、值得玩味的细节,但却并不会给人以琐碎之感。尤其是一开头那一段忧伤而略带凄惶的音乐伴随着摇曳的摄影机镜头在巴黎街头摇晃,虽然这一段时间较长,但除了能很好地渲染气氛、带出故事发生的场景外,也仿佛是在以安东尼迷茫地游荡在街头的摇曳视角来审视、观察巴黎和这个世界。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恰恰让此片更具儿童电影的特色。
此外,对于电影中塑造的安东万这般“问题少年”的形象,还可以有更深刻的文化反思。安东万向往大海,向往自由、追求自我,却因个性反叛而失去自由、被关进劳改中心,努力逃出劳改中心后他却并未重获自由。尽管他最终逃到了他一心向往的、代表着自由和自我的大海,却在抵达海边时发现,恰恰是大海阻断了自己的去路,是“逃亡”现实、“逃脱”社会的离经叛道之路上的无法逾越的阻碍和限制——他只能回头,而他回头后那一脸茫然、困惑、矛盾的表情也在片末定格下来,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一幕。
劳改中心设在海边,或许本来就有防止犯人外逃、便于“追捕”的考虑,这是合情合理的另一方面,似乎这也是一种隐喻——无拘无束的“自由”和不受束缚的“自我”是吸引我们不断“叛逃”的“大海”,但同时也是阻碍我们“叛逃”的障碍和限制,我们最终还是要被迫回归现实、回归社会,去面对很多不愿面对的事情、做很多不愿做的事情。
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其实每个人都曾经是个渴望叛逃的孩子,都有想要“出逃”社会与现实的冲动,都曾渴望无拘无束的自由、保持真实的自我,但却又不得不一再妥协、“挨打”、改变自己、适应社会的规则,在不停地“叛逃”与“回归”中逐渐变得“成熟”、“世俗”,学会遵守规则、控制自己的言行。尽管人的本性里都是追求自由、讨厌束缚的,但“自由”恰恰也会是一种束缚和阻碍。
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仅是安东万的困惑、“问题少年”的困惑,也是现代人的困惑,“现代性”带来的人性困惑。“现代性”“规训”了人的思想和身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每个现代人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安东万的这种“反抗与依附”、“叛逃与回归”的纠结、挣扎、矛盾和困惑中,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逐渐了解社会、接触社会、最终步入社会,始终在努力地适应社会与坚守自我、追求自由中取舍、权衡、摇摆而逐渐变得“成熟”的成长过程。
福柯认为,“惩罚”和“约束”都只是控制人的方式,都是作用于身体之上的政治技术。“如果说法律现在必须用一种‘人道的’方式来对待一个‘非自然’的人(旧的司法以非人道的方式来对待‘非法’的人),那么这不是由于考虑到罪犯身上隐藏着某种人性,而是因为必须调控权力的效果。这种‘经济’理性必定要计算刑罚和规定适当的方法。‘人道’是给予这种经济学以及锱铢计算的一个体面的名称。‘把惩罚减到最低限度,这是人道的命令,也是策略的考虑。’”从酷刑到规训的转变谈不上“人道”不“人道”。现代刑罚体系背后的“规训”系统虽然看似温和,事实上恰使权力运作得更经济、更有效、更制度化,如毛细血管般更加深入社会肌体,最终强化了权力的实际控制效果。
在福柯看来,在近代以来的新式教育、军队,以及劳改所中,这种“规训”权力运作得最为典型。他在此书一开篇还列出了一份十九世纪初的“巴黎少年犯监管所”中犯人的具体作息时间表,并提出,这代表了近代以来的一种新型权力运作方式——“规训”。而《四百击》中严酷的老师、严格的课堂规定、体罚、对学生身体与思想的高度控制,都让我们意识到,这就是福柯所说的那种作为典型的规训范例的课堂;影片中反复暗示的安东万对军官学校严酷训练的恐惧、他继父对他“只要我还养你,你就必须听我的话,否则我们就送你去陆军军官学校……他们会让你站军姿!”的恐吓,也让我们感受到,片中的军官学校就是福柯笔下的那种作为典型规训机构的军队;影片最后展现的安东万在少管所的生活——列队齐步走、必须严格遵守规定、不许擅自提前用餐、违者受罚……活灵活现地将福柯所描绘的那种作为典型规训机构的少管所搬上了银幕。
在“规训”权力运作的过程中,对身体的控制、对自由的限制、“全景敞视主义式”的密切监视、意识形态控制与心理干预等,都是极为重要的手段和工具。但我们来看看《四百击》的主人公安东万长期以来的生活状况吧——他父母由于忙于工作而对他疏于管教、看管,对他的“监视”、“限制”、“约束”不足,亦不能同他进行有效的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无法走进他的内心;而学校对他的身体控制、自由的限制、监视看管、交流沟通也很非常不足,这就导致他“太过自由”而未被顺利地加以“规训”。在父母、学校都不能完成对他的“规训”时,社会就只能将他交给少管所来进行高强度的专门化“规训”,所以他父母要签署一份“把做父母的权利移交给少管所的书面申请”,而他也不能再继续上学——这其实意味着将他的“教育权”、“监护权”正式从父母和学校那里移交给少管所。在这个意义上,《四百击》对少年、人性的“现代性”问题的独特反思,或许可以视为是对福柯“规训”理论的一种艺术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