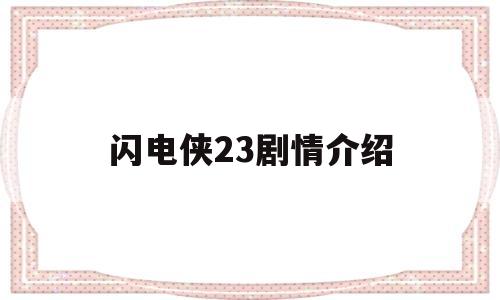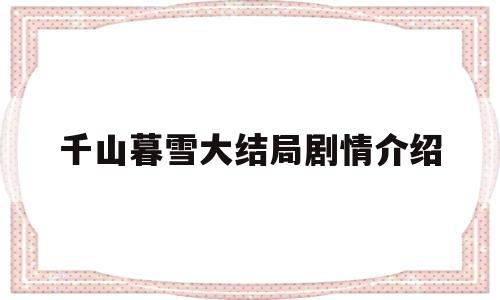复仇是一盘放凉了才好吃的菜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掀起一场“完美”暴风雨
文/倏尘
诺贝尔文学奖有力竞争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根据莎翁临终作品《暴风雨》改写了一部小说——《女巫的子孙》。改写莎士比亚似乎很容易被读者贴上“油嘴滑舌、插科打诨”的标签。然而,阿特伍德却将这部带有暗黑色彩的戏剧,改成了一个戏剧家与囚犯导演的一场复仇故事。而小说中监狱的隐喻,复仇的喜剧性,却被阿特伍德营造出的戏剧化情节,很大程度折射出莎士比亚的戏剧风格。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改写的故事让复仇成了一场终将平息的暴风雨。“不管仇恨来势多么猛烈,终会像暴风雨一样平息下来。”作者是这样说道的。
和莎士比亚许多广为人知的剧作相比,《暴风雨》在国内的知名度也许并不高,但它的精彩程度却毫不逊色。不像四大悲剧,《暴风雨》里没有杀戮,所有人的性命都得到了保全。不像《裘力斯·凯撒》,《暴风雨》里也没有那种快意恩仇、直面生死的浩然正气,而是混杂着仁慈、宽恕、希望、释然甚至有点孤寂和虚无的情绪,反映出莎士比亚日臻成熟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晚年对待人世无常的心境。在时间上,这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最后一部戏。它魔幻、诡谲,又现实、深刻,引人遐想、回味无穷,足以代表莎翁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座巅峰。
由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根据《暴风雨》改写的小说《女巫的子孙》继承了原作的基本脉络,将这部经典用现代的方式再次呈现在读者面前。虽然故事的环境发生在现代,但作者并没有以现代之名胡乱篡改,相反却处处精心设计,尽力向读者讲好《暴风雨》的故事,并在这一基础上阐发新意。这说明阿特伍德在写作时始终非常清楚霍加斯出版社给她布置的这个半命题作文的初衷——利用改写致敬莎翁,利用改写拉近经典与大众的距离,利用改写展现一个作家对莎士比亚的独到见解。
在小说开始前,本书安排了原剧剧情概述,可以让不了解《暴风雨》的读者对原作情节和主要人物有一个基本了解,并且在阅读小说时可以随时翻看、比对。小说仿照原剧台本的形式开场,随后进入主线,其中安排了一些剧中剧的结构,共同指向《暴风雨》里的情节。
主人公菲利克斯被戏剧的魔力控制住了,就像《暴风雨》中沉溺于法术的普洛斯彼罗。而更可怕的是,那时他还没有料到,自己会因此失去唯一的女儿和视为生命的导演权力。菲利克斯没有机会经历海难,但是他的人生也在一瞬间倾覆,沉入绝望的海底。在自我放逐了十二年后,他也决定抓住机会复仇。不过他没有普洛斯彼罗的法术,他手中紧握的仍然是戏剧的魔力。
而这一次,他决定借助罪犯演员的力量,在监狱这一绝佳的幽禁场所,再现他一直渴望搬演的杰作《暴风雨》。主人公不仅要惩罚仇人,看着他们痛苦地呻吟,还要重新点亮他的戏剧梦想、召唤他死去的女儿。最终,菲利克斯上演一出全浸入体验的戏中戏,也正如他自己是在用生命全浸入体验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一般完美。
有传言阿特伍德的确有女巫的血统
故事的嵌套应该说是阿特伍德的长项,她在《盲刺客》《使女的故事》等作品中就大量使用,《女巫的子孙》相比之下被处理得得心应手。
小说的语言诙谐幽默,带有十足的阿特伍德风格。阿特伍德的语言明快、利落,喜欢对人的意识流以及周遭世界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甚至偶尔有些絮絮叨叨。她在天气、颜色、气味、建筑、人物穿戴等方面有着惊人的想象力和无比丰富的修辞,这一点在本书中也有所体现。她根据原剧情节创作的几首自由体诗歌,读来轻快活泼,很好地诠释了《暴风雨》长久以来可被视为一部音乐剧的传统,也从某种程度上还原了莎剧“戏中有诗,诗中有戏”的特点。不过,和另一位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相比,阿特伍德似乎不擅长温婉细腻的情感描写,所以小说在人物内心世界的塑造上略显粗枝大叶。
小说的主题是多重的,有仇恨与宽恕、幻象与现实、爱与政治、囚禁与自由等多种解读可能。小说通过设置一个在监狱里教授文学的课堂,通过主要人物之间的对话,对一些重点主题进行了分析。不过,单从小说名“女巫的子孙”来看,作者似乎是有意触及该剧涉及的另一个传统主题:文明与野蛮。
《暴风雨》中的凯列班(俄)吉那第·史比伦
“女巫的子孙”指的是剧中半人半兽的怪物凯列班,他是死去的女巫西考拉克斯的儿子,在普洛斯彼罗来荒岛前是这里的原住民。他被普洛斯彼罗奴役后,一直记恨这个借法术夺走他海岛的人,并且对普洛斯彼罗的爱女米兰达图谋不轨。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野蛮、粗鲁、兽性、残暴的,但他也有天真、直率、单纯、可爱的一面,例如他常常会对海岛发出由衷的赞美,对音乐和大自然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有人认为,凯列班这个名字是英文单词Cannibal(食人者)被重新排列后创造出来的,反映了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人对新大陆原住民的态度。在本剧创作的17世纪早期,欧洲人对世界的探索在持续进行,伦敦经常会传来探险家和殖民者在某个新大陆遇到原住民的故事。这些原住民常常被描述成茹毛饮血的野蛮人,他们同族相残,甚至会食用对方的身体,和文明发达的欧洲白人相比完全不在一个进化等级。
凯列班是“野蛮的代表”
但与此同时,一些人对欧洲的自我中心主义也进行了反思,例如蒙田在《论食人族》中就说,“这些民族的野蛮是因为他们极少受到人类思想的熏陶,仍然十分接近他们原始的淳朴”,而人类“作恶的本领比他们大得多”。他说,这些所谓的蛮族对于他们的俘虏其实是十分优待的,杀死时是“用剑柄打死”,然后吃死者的肉。
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19世纪,诸如柯勒律治等诗人对凯列班赞赏有加,认为他是一个“高贵的生物”,相比其他人更淳朴真实,身上流露着真性情。到了20世纪,随着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凯列班又成了反抗普洛斯彼罗这样的殖民者的楷模。所以,西方世界对的文明与野蛮的反思始终存在,“女巫的子孙”一词背后隐藏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2010版《暴风雨》电影中的凯列班也让观影的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而在小说中,犯人们对凯列班的喜爱也显而易见,他们为歌颂“女巫的子孙”所创作的诗歌,一方面是在为凯列班这个传统上被文明世界唾弃的“野蛮人”正名,另一方面也是在为他们这些被社会抛弃的“底层人”正名。他们虽然有罪,有些还是暴力的歹徒,但他们从“女巫的子孙”身上找到了某种共鸣,那就是他们也有淳朴、自尊、向善的一面,他们渴望社会承认这一面。通过菲利克斯开设的莎翁戏剧课,他们找回了人性中失落的美好和自信,这才敢于喊出“我们是女巫的子孙”这样的豪言。而《女巫的子孙》在原剧中所承载的人文价值,在小说现代语境的化学作用下,也焕发出新的光芒。
当然,上头这些冗长的学术背景自然没有出现在《女巫的子孙》中,但如果仔细阅读小说,阿特伍德处处都留了线索,等待好奇心强的读者自己去探索。作为曾在文学系任教的大学老师,阿特伍德确实会忍不住借人物之口讲一些关于戏剧的知识,关于《暴风雨》的认识,这也是她良苦用心之所在。
记得亚马逊上有人评论说,自己读这本书时感觉阿特伍德一会儿是作家,一会儿又成了文学课堂上的老师。当时就捂嘴一笑——这位老兄真是看进去了。这不正是阿特伍德这位文学女巫施展的魔法,也是《女巫的子孙》最独特之处吗?